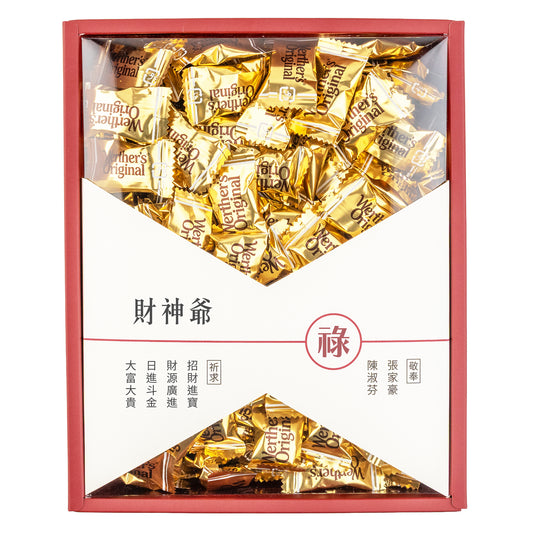5大認知錯覺揭露大腦如何悄悄扭曲現實世界,教你重啟感知力。
Share
你的大腦並不是在「看」世界,而是在「發明」世界。歡迎來到感知的奇異科學──以及當錯覺出錯時,該如何修正。
當你閱讀這篇文章時,大腦正在替你建構一整個世界。
當你一邊滑動這篇文章,你的大腦正忙著創造你所活在其中的「心理世界」。你大概感覺自己是很自然地嵌在一個充滿他人、物體,以及自己思緒的世界裡,而且一切流暢無縫。
在你讀完這一句話的時間裡,你的大腦已經快速解碼感官總匯(sensorium,也就是接收並詮釋感官資訊的那一部分)中的資料,把螢幕上的這些形狀,轉換成你腦中浮現的「聲音」。但不只如此,它同時也在做更深、更快的判斷。
舉例來說,雖然我們素未謀面,你的大腦很可能已經對我做出一些快速的假設,尤其是在我用了像 sensorium 這樣的字之後。(學術派?沒錯。做作?就交給你來判斷。)
或者,這個字也許引發了更內向的一種反應:你對自己是否真的懂得 sensorium 這個詞,感到很有把握,或是有點心虛不安。
身為一位心理學家與神經科學家,我的工作,就是去理解大腦如何完成這個驚人的魔術──它究竟如何建構出一個「外在世界」的幻象。
而且,我和同事們認為,我們找到了非常激進的一個答案:你的大腦,其實很像一位科學家。
就像科學家會建立理論來理解世界一樣,你的大腦也會產生自己的假說,來詮釋所謂的「現實」。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你會覺得大腦的運作又快又不費力。不過,這種做法雖然有效率,卻也有代價:它讓我們的大腦很容易看錯、也很容易相信錯的東西。
每個人其實都活在一個「版本化的現實」裡,而那個版本是由我們自己的假設與預測所塑造的。意識到大腦對我們耍的這些小把戲,可以重新改變我們理解自己的方式,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和那些「看世界方式不同的人」相處。
以下是你的大腦用來建構「你的版本的現實」的幾種關鍵方式──以及你可以如何把這些現象轉化成自己的優勢。
1. 你的世界,其實是一場幻覺。
我們通常會以為,大腦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幅大致正確的世界圖像。畢竟,我們會假設「看到不存在的東西」或「聽到不存在的聲音」,代表我們精神出了問題。但最新的研究顯示,事情並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所有人隨時都在「產生幻覺」──而大腦提出的理論,會決定我們到底看見了什麼。
你可以從我書本封面上的那個錯覺例子看到這點。大多數人都會覺得那顆蘋果是紅色的,但實際上它是灰色的。
你之所以看到紅色,是因為你的大腦對「蘋果」以及它「應該是什麼顏色」有一套理論。你真正看到的是這套理論被投射出來,而不是螢幕上那些實際的像素。
如果我們把你放進核磁共振掃描(MRI)儀器裡,即使外界什麼都沒有,我們也能看見你的大腦正在創造自己的假設與期待。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給你看一張照片,但刻意挖掉其中一大塊,照理說在那一塊上,大腦中負責視覺的區域應該是安靜的;但實際上,它會亮起一種神經活動的圖樣,長得很像你大腦「認為那裡應該要有的東西」。我們可以即時看到,你的大腦如何在視覺空間的畫布上,把空白的地方補起來。
這個過程通常非常有幫助──但它也讓我們的大腦帶有一種內建的「愛發明」傾向。
意識到我們所有人都可能「看到」或「聽到」不存在的東西,可以讓我們用全新的角度看待更嚴重的幻覺現象──例如精神病患者的幻覺經驗,或自稱聽見超自然聲音的靈媒。
科學家認為,那些有強烈幻覺的人,可能只是比較容易讓自己的假設與理論「溢出」到感知當中。
重要的是,看起來「產生幻覺」與「罹患心理疾病」,牽涉到的大腦網路並不相同。
所以,如果你曾經有過幻覺,那並不代表你的感知系統出了問題。幻覺並不是系統的故障──它是大腦運作方式的一個核心特徵。
2. 你其實沒有真正在聽別人在說什麼
你有沒有在 KTV 搶過麥,盯著螢幕上的歌詞跑動,才突然發現自己其實已經錯聽這首歌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了?你絕對不是唯一的一個。
很多人都會經歷所謂的「mondegreens」,也就是誤聽歌詞──例如把 Nirvana 歌詞聽成「here we are now, in containers」,或把 Elton John 的歌聽成「count the headlice on the highway」。
這些誤解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們很少真的「聽到」別人講的精確字句──我們多半只接收到大腦對「對方大概想講什麼」所做出的最佳猜測。
這聽起來或許有點沒禮貌,但原因在於,你的大腦根本不會閒著等別人把話說完。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點,是因為當研究者錄下許多人用各種語言交談時,他們發現對話中輪流發言之間的平均間隔時間短得驚人──大約只有 200 毫秒(五分之一秒)。
為了跟得上這種速度,你的大腦必須先跳到前面預判──在說話的人還沒說完之前,就先產生各種句子可能結尾的假說。我們甚至可以在你聽自然語音時,直接在大腦裡看到這個過程。
例如,當你聽到一句話開頭是「in the hospital there is a newborn…」,核磁共振掃描會顯示,你的大腦在「baby」這個字真正被說出口之前,就已經激活了一個類似「baby」的神經活動圖樣。
3. 你並沒有像自己以為的那麼有掌控力
我們的大腦常常會誤導我們,讓我們以為自己對世界的掌控力,比實際上多或少。心理學家稱之為「掌控錯覺」(illusions of control)的現象,就是我們覺得自己要為某些其實無法影響的事情負責。
以「安慰劑按鈕」為例。在許多城市裡,行人穿越道、電梯,甚至辦公室的溫控器上,都有一些其實完全沒有作用的按鈕──真正的系統其實是由電腦或定時器控制的。但人們還是會去按那些按鈕,卻不知道它們根本沒有效果。
他們之所以覺得自己有在讓車子停下來、或改變室溫,只是因為他們「預期」自己應該做得到。
不過,比起這種「假掌控感」的趣味,也許更讓人擔心的是相反方向的誤解:「被動錯覺」(illusions of passivity)──也就是當我們實際上要負更多責任,卻感覺不到。
在社會情境中,這些錯覺會變得很危險,例如當人們覺得自己只是「服從命令」。有一項研究就看了這種情況下,大腦會發生什麼事:研究者比較了人們「自行選擇」傷害他人,和「被命令」去這麼做時,大腦反應的差異。
如果受試者是自己選擇為了小小的報酬而對同伴施以(輕微)電擊,他們的大腦在聽到電擊聲時會亮起反應──這代表他們正在登錄自己行為的後果。但當他們是「奉命」施加同樣電擊時,大腦的反應就會變弱。
彷彿在把責任交出去的那一刻,大腦真的就對自己行為的效果「調低了音量」。
好消息是,這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可以訓練自己更願意承擔責任,並且擁有更貼近現實的掌控感。在另一個版本的電擊實驗中,研究者找的是比利時一所軍事學院的受訓軍校生。
儘管他們受訓的其中一項重點是「服從命令」,這些軍校生在處理自己行為的方式上卻不太一樣,因為他們同時也被訓練,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所以,即使當他們是在「被命令」的情況下造成傷害,他們的大腦仍然顯示出「行動者」以及「意識到後果」的跡象──無論選擇是出於自由意志還是服從命令,他們的神經活動都反映出:自己知道正在做什麼。
軍事訓練當然不是適合所有人的選項,但這些結果揭露了一件關於我們所有人的重要事實:我們的掌控感,是經過大腦理論「過濾」之後的產物。我們感受到的,不一定是自己實際擁有多少掌控力,而是「大腦覺得我們應該感受到多少」。
正如這些軍校生所示範的那樣,透過經驗與社會學習,我們有可能重新塑造這些信念,連同我們對「自己行動到底有多重要」的感覺,一起改寫。
4. 你的肢體語言,其實是一種「身體方言」。
你也許認為自己很會讀肢體語言。如果一位同事笑著、幾乎用跳的走過走廊,而另一位只是拖著步伐經過,要猜誰升官,應該很明顯吧?
但情緒並不是直接從一顆大腦「投射」到另一顆大腦上的。想想下面這個研究中的示意圖:心理學家讓受試者看幾張網球選手的照片──一個看起來像是贏家,另一個則像是落敗者。
但其中有個關鍵轉折:這些照片上的臉其實完全一樣,是數位複製再貼到不同身體上的。你只是根據那張臉「應該搭配什麼姿勢」的預期,用身體姿態去補上情緒的意義。
這告訴我們一件關鍵的事:我們並不是「直接」看到情緒。我們是根據整體畫面──以及自己的預期──去詮釋情緒。
我們很容易假設別人表達情緒的方式跟我們一樣,但通常只有在對方的身體節奏和我們相近時,我們才會判斷得比較準。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研究發現:當別人的「自發性動作節奏」(spontaneous motor tempo,也就是行動速度)跟我們差不多時,我們比較能準確辨識他們的情緒狀態──不論是開心、難過,還是生氣。
走路速度快的人,通常也比較容易打拍子或揮手揮得很快,而這種節奏會變成一種個人的「方言」,用來表達情緒。
這些不合拍的「方言」,可以解釋很多日常生活中朋友、伴侶、同事或家人之間的誤會。它們也可能說明了經典的親子衝突:青少年和父母之間的張力。
隨著年紀增長,我們身體的節奏會變慢,因此表達情緒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這代表每個年齡層都比較習慣「自己那一群人」的節奏──所以在大人的眼中,青少年常常顯得過度亢奮或過度激動;而在青少年的眼裡,大人又顯得憂鬱、冷淡或提不起勁。
我們的大腦於是讓我們「感覺」:青少年就是太情緒化,而父母永遠對我們不滿──光是這樣,就足以讓親子之間不斷起衝突。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幫助我們在「神經多樣性」的世界裡,更好理解彼此的溝通落差。很多年來,科學家都以為「自閉傾向者」在理解他人方面比較吃力。但後來發現,溝通不良其實是雙向的。
例如,有研究顯示,自閉者的動作方式通常不太一樣──他們的手勢往往更突然,或加速得更快。
同樣的研究也發現,即使在請自閉參與者表達更複雜的情緒時,這些差異依然存在,例如在請他們演出一則關於「說服」或「欺騙」的故事時也是如此。
在實驗室情境中,自閉參與者有時確實比較難解讀「神經典型」(neurotypical)對象想傳達的想法與感受──但神經典型的參與者,也同樣很難讀懂自閉者。
如果我們把每個人都想成是在用自己的身體濾鏡來解讀他人,這一點就變得非常合理。也就是說,把一個人簡單貼上「很會共感」或「不會共感」的標籤,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真正關鍵的是:對方到底有多符合,我們大腦已經替我們建立好的那一組「情緒與身體方言的棱鏡」。
5. 鏡子裡的自己,是大腦為自己寫的理論。
大腦不只是在幫我們向外看,用來理解物理世界與他人,我們也會用它向內看。
但理解自己,其實跟讀懂別人一樣容易出錯。事實上,你的自我形象,是由大腦對「你是誰」這套內在理論所塑造出來的。
這套理論的核心是「信心」:也就是你對自己決定與行動的主觀篤定感。然而,大腦其實很難準確算出,你「應該」感到多有把握、或多不確定。正因如此,它會高度依賴你的過去經驗與既有期待。
在我們的實驗裡,例如,我們發現人們在「過去曾成功」的情境中,會感到更有自信;而在「先前曾經吃力」的情境中,會覺得更不確定──即使這兩種情況下,他們實際表現得一模一樣。
換句話說,當我們向內檢視時,我們感受到的,其實是大腦「預期」我們會有的信心程度,而不是真正反映我們的天賦、潛力或能力。
某種程度上,這就像大腦創造出的其他錯覺,只是它往往帶來更糟、也更持久的後果。
這些內省偏誤會變得自我強化,讓你被卡在一種固定的自我看法裡。
如果你過去比較幸運,你的大腦就會把比較樂觀的期待寫進你的自我形象,給你足夠的信心去奮鬥、去成功。
但如果你過去比較不順利,大腦可能會把更悲觀的預測烘焙進你的經驗裡,讓你覺得自己不確定、做不到,進而削弱你再試一次的動力。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成功會生出更多成功」。
有一項研究就發現,那些在第一個研究計畫經費申請上「勉強拿到補助」的科學家,相較於那些「在第一輪就被些微差距淘汰的人」,在接下來的職涯中累積到更多經費。
但這群「幸運得標者」和「不幸落選者」之間的差距,多半來自努力程度,而非天分──很多落選者後來乾脆不再申請。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些好運或壞運,會牢牢刻進大腦那套「我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模型裡。
這些發現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我們主觀感受到的信心(或缺乏信心),其實很可能會誤導我們。
這也讓我們對某些心理狀態有了新理解,例如憂鬱症。有些心理學家認為,憂鬱症的燃料之一,就是主觀信心的全面下滑,即使我們客觀上的技能與能力其實好端端地在那裡。
憂鬱的想法與感受,可能正好是在我們的大腦被一套「悲觀版本的自我理論」卡住時,開始緊緊抓住我們的。
但關鍵在於:理解這件事,本身就能幫助我們打破這個循環。
當我們開始承認,大腦並不總是對我們有正確認知──而且即便感到懷疑,仍然值得繼續嘗試──我們就會對新的經驗與潛在的成功打開大門,讓它們進來,更新大腦對自己的模型。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更貼近事實、也更完整的「真正的自己」。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