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伴臨終病人:以溫柔好奇與尊重記錄死亡經驗與對話全程細節
Share
研究臨終歷程如何加深我們對日常存在的理解
重點摘要
-
深度傾聽臨終者,是向他們踏入我們終將抵達的邊界旅程致敬。
-
帶著系統性的好奇心面對死亡經驗,既是尊重,也能加深我們的理解。
-
精確記錄臨終者的敘述,不急著下判斷或詮釋,是研究與陪伴的關鍵。
Sergei Rachmaninoff 的臨終時刻
Sergei Rachmaninoff 在他位於 Beverly Hills 的家中奄奄一息。家人和朋友圍繞在側,房間裡瀰漫著一種特有的寂靜,那往往伴隨著生命最後幾個小時而來。接著,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發生了。這位作曲家睜開眼睛,問在場的人:「你們聽得到這段美妙的旋律嗎?這極其美妙的音樂?」
床邊眾人的反應十分直接:「沒有,這裡沒有音樂。」
Rachmaninoff 堅持說:「有啊,你們真的聽不到這段美妙的旋律嗎?它是那麼……」
其他人仍說:「沒有、沒有,這裡什麼都沒有。」
最後,Rachmaninoff 讓步了:「好吧,那這音樂就只在我腦中。」
他重新躺下,然後離世。
我們本可以學到什麼
在我多年研究死亡與臨終心理的過程中,這一幕始終萦繞在我心中。原因並不在於 Rachmaninoff 究竟聽見了什麼——那點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而在於這個情境所代表的錯失機會。當時若有人問一句:「你聽到的是什麼樣的音樂?你可以描述一下嗎?你能哼出來嗎?我們可以把音符記錄下來。」這會付出什麼代價呢?
在多重層面上,這個場景濃縮了我們在研究中不斷面對的一項挑戰:當有人報告一種與我們自身感知不相符的經驗時,我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修正對方,而不是探索。「不,不是那樣。」幾乎總是比「請多說一點」來得快。然而,在這個專門研究生命邊界的領域裡,這些「異常經驗」可能正是最有價值的資料來源。即便不把它們視為數據,至少也是一次溫柔人際相逢的機會。
我會把這個故事分享給所有希望參與我們研究的人,並列為必讀材料,只因我不希望我們重蹈覆轍——說出「不,這裡沒有音樂」,而不是問「你聽到了什麼?」這並不表示我們要將資訊提供者說的一切全盤照收,視為客觀或本體論上的真實與正確。有時,就連提供經驗的人自己也不這麼認為。相反地,他們會說:「這是我正在經驗的事」,或「這是我曾經經驗過的事。」但光是這一點,有時就足以向我們拋出真實而艱難的問題。
現象學立場
當我們研究臨終病人所經歷的事、觀察所謂的「臨終清明」(terminal lucidity),或聆聽回報瀕死經驗(near-death experiences, NDE)的人時,我們處在一個頗為特殊的位置:我們試圖理解的是一些我們自己尚未親身歷經的意識狀態。
我們與這些狀態的真正相遇還在未來;在場的研究者沒有一個人能以自身體驗對受試者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我也經歷過同樣的事。」我們頂多能說,我們曾觀察或聽人描述過這樣的情況——然而那仍只是一種只能由第一人稱視角真正把握的經驗。David Hume 曾如此表述:在你真正吃過鳳梨之前,你永遠不會知道鳳梨是什麼味道。仔細想想,這句話既顯而易見,又相當深刻。那麼,當對方尚未經歷某件事時,我們究竟要如何分享我們所經驗到的?
我們所研究的人,接觸到的是一些我們只能透過他們的報告來接近的東西——而即便如此,也依然困難,因為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幾乎不是為了這些特殊的臨終經驗而創造的,也很難具備足夠的詞彙來描述此類非尋常狀態。這是其一個挑戰。
語言幾乎總是顯得力有未逮,而當你與這些經歷過極度特殊體驗的人交談時,會一再遇到這一點。他們反覆說:「我可以試著這樣描述,但總覺得哪裡不完整。最關鍵的部分像是缺了什麼,因為我找不到對應的字。」
另一個挑戰則在於:即便是我們勉強能理解的部分,本身也往往已經相當非凡。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位瀕死經驗的回報者曾神采飛揚——真的可以說是神采飛揚——地告訴我,在她的 NDE 中,她看見了四種顏色——她是一位畫家,說自己「發現」了這些顏色的存在——「這些顏色我們在地球上沒有」,或者更精確地說,「我們的眼睛在『這裡』沒有辦法看見。」
這就造成一個方法學上的難題:我們要如何處理那些我們既看不見、也無法直接驗證的事物、狀態與事件?我相信,答案不一定在於「驗證」本身(儘管在某些案例中,這仍然是重要議題),而更在於謹慎且開放的記錄。當一位晚期 Alzheimer’s 病人,在臨終前幾小時突然清晰、連貫地說話時,最沒有建設性的反應,就是急著把這一切合理化、解釋掉。對科學而言,更有趣、更具價值的回應,是儘量把一切記錄下來:他們說了什麼?怎麼說的?他當下的意識狀態看起來有什麼不同?
以系統性的好奇心來傾聽
在過去二十多年研究死亡與臨終心理的過程裡,我學到、也希望與所有打算加入我們研究的人分享的一件事,是一種可以稱作「系統性好奇心」的態度。
換句話說:當有人說自己聽到別人聽不到的音樂,或經歷出人意表的清明時刻時,我們仍然有選擇可以做。我們可以把這些全都視為幻覺、藥物副作用,或大腦缺氧所造成的結果。但這種做法既幫不了當事人,也無助於維持與那些「看見或聽見了別人暫時還沒(或永遠不會)接觸到的東西」之間的對話。或者,我們也可以選擇小心、完整地記錄這些經驗,不急著替它們貼標籤、下結論。
試著想像,如果當時陪在 Rachmaninoff 身邊的人是這麼回應他的:
「你們聽得到這段美妙的旋律嗎?」 「我聽不到,但告訴我——它聽起來是什麼樣子?」 「它美極了……不像我寫過的任何作品,卻又有種熟悉感……」 「有樂器嗎?有人聲嗎?」 「兩者都有,又好像都不是……很難形容……」
這樣的對話,或許會讓我們得到一些關於臨終意識現象學的珍貴資料——說不定還會因此多了一部來自 Rachmaninoff 的遺作(如果這音樂真的只存在於他的腦中),或者一首「不知何處而來」的作品(如果這音樂在某種意義上真的「存在於某處」)。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互動會讓 Rachmaninoff 得以分享他的經驗,而不是被封閉在那個無人能懂的世界裡。
異常的科學價值
Thomas Kuhn 曾描述科學典範如何發生轉變——通常是因為某種不斷累積的「異常」,讓現有理論無法再自圓其說。在我們的研究領域裡,臨終床邊的種種經驗充滿了這樣的異常現象。每當我們遇到這些異常時,我們可以選擇硬把它們塞進既有的分類裡——或者,也可以讓它們暫時就這樣存在,原原本本地呈現為它們自己:一種挑戰我們理解、並邀請我們進一步探究的現象。
醫學史上處處可見那些先被忽視,後來才被理解的現象。醫師們曾經嘲笑「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生物會造成疾病」這樣的想法。曾有人覺得「潰瘍是由細菌引起的」這種說法荒謬不經,直到 Barry Marshall 親自感染自己,才證明這一點。許多起初看似不可能的事,最後卻變成理所當然——前提是,必須有人願意把這些異常當成真正值得研究的對象。
對我們工作的實務啟示
-
接受經驗本身,照其所是。 若有人說自己聽到了音樂,無論現場有沒有可測量的聲波,至少有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那個「聽見」的經驗確實存在,而它就值得被記錄下來。在哲學上,我們稱之為「不可推翻性」(incorrigibility):你無法單憑一句「不,你沒有看到那個!」就推翻一個人的主觀經驗,即便那是幻覺。經驗不必與外在現實對應,才能構成自己的真實——從第一人稱的視角來看,它就是那個人當下的整個世界。
-
不帶評斷地追問細節。「那是什麼感覺?」「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麼嗎?」「這種情況以前發生過嗎?」這類問題能讓我們獲得豐富的現象學資料,同時也在向當事人傳達:他的經驗是被承認、被認真對待的。
-
精準記錄。 準確寫下人們說的原話,而不是直接寫成我們的詮釋。如果有人說:「我母親在這裡」,不要立刻寫成「病人出現視覺幻覺」。詮釋可以之後再做;我們首先需要的是盡可能忠實的資料。
-
延後解釋。 立刻分類與解釋的衝動非常強烈,但太早下結論往往會讓我們看不見真正正在發生的事。在這些經驗被納入某個理論架構之前,先允許它們純然地呈現為「現象」,是必要的步驟。
超越方法之外:溫柔地在場
還有另一個層面,超出了方法學,卻與尊重與人性尊嚴密切相關。當一個人臨終,向我們分享一些看起來不可能、甚至只是不太可能的經驗時,他們正在敞開自己,也許是在分享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驗。
要為自己擬一個不錯的回應準則,其實可以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你自己,而你正在向別人描述這些臨終經驗,你會希望對方怎麼回應你?
臨終者接觸到的是一種意識狀態,其他人目前只能以第二手方式加以研究。他們像是被迫踏入一片我們終究也會走進去的未知領土的探索者。而我們至少能做的,是認真、專注地聆聽,細心收下他們從那個邊界帶回來的每一份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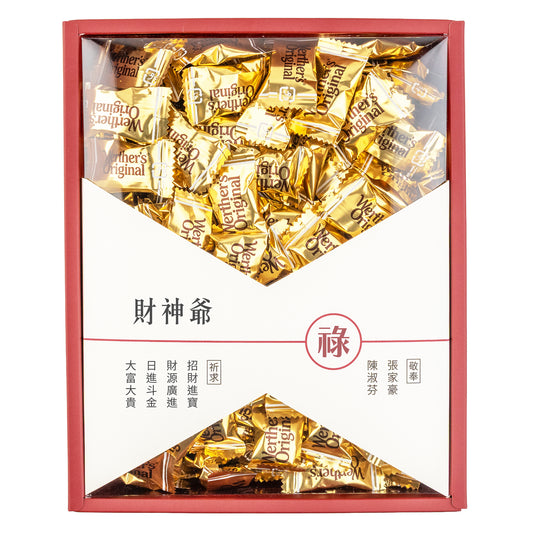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