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hony Hopkins 自傳專訪:戒酒、上帝與人生
Share
Anthony Hopkins 談戒酒與找到上帝
在 Anthony Hopkins 許多最偉大的表演中,他總能為角色注入引人入勝的隱秘深度。那些魔法就存在於他們所知道的、觀眾所知道的,以及這些角色願意表達之間的空隙。無論他是在他三部 Hannibal Lecter 電影中飾演操縱性的怪物,或是在令人心碎的〈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扮演情感上羞怯的管家——那是我最喜歡的他的作品——這些男人正在思考、正在感受一些事,而由於種種原因,他們將其保留在心。
對 Hopkins 來說,情況已不再如此。在他的新回憶錄《We Did OK, Kid》中——將於 11 月 4 日出版——這位 87 歲的人分享了他在威爾斯艱難的學校歲月、他看似奇蹟般戰勝飲酒問題的經過、他與唯一孩子痛苦的疏離,以及他緩慢而穩定地走向好萊塢成功的歷程。
這本書也揭示了一位有些內斂而孤僻的人,但他並不滿足於僅僅敘述他多年的事件、發生了什麼與何時發生。他對那些大哉問——一切為何,以及這一切意味著什麼——投入了深刻思索。然而,即便在生命的這晚期,Hopkins 仍對他稱之為人生的夢的幸運與不可能性深感美好地困惑。
我們的人生都有轉捩點,但你的轉捩點格外具體——一個改變你一切的時刻。你能告訴我 1975 年 12 月 29 日 11 點發生了什麼嗎?
我總有點不太願意談這件事,因為我不想聽起來像在說教。但我當時喝醉了,在加州開車、處於斷片中,完全不知自己要去哪,這時我意識到我可能會撞死某個人——或者撞死我自己,而我其實不在乎——於是我意識到自己是個酒鬼。我回過神,對我在比佛利山一個派對上的一位前經紀人說:「我需要幫忙。」當時正好 11 點——我看了我的手錶——而這就是毛骨悚然的地方:某種深沉而強大的想法或聲音,從我內心對我說:「一切都結束了。現在你可以開始活了。而且這一切都有其目的,所以別忘了任何一刻。」
那只是個憑空而來的聲音?
從我內心深處。但它是有聲音的、男性的、理性的,像個電台的聲音。對酒的渴求被從我身上帶走了,或是離開了。如今我沒有任何理論,除了神性,或是我們每個人內在擁有、從我們出生就創造我們的那股力量,生命力,不論它是什麼。我相信那是一種意識。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要不要我再給你一個頓悟?
好。
一九五五年,復活節。我的成績單到了——那可怕的成績單。我 17 歲,害怕這一天,因為我父母會看到那些可怕的成績,因為我就是個笨蛋。我被叫做 Dennis the Dunce,完全搞不懂正在發生什麼。怨懟、孤獨,諸如此類。我記得我父親大約在傍晚 5 點打開成績單。我們正要去看一部電影。美麗的春日。他打開成績單,上面寫著:「Anthony 遠低於學校的標準。」那其實就是宣判死刑。父親說:「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樣。」他很擔心,而且相當合理,因為他花了一些錢讓我受教育,而我達不到那個標準。但我記得我微微退了一步,然後我說:「總有一天我會證明給你看。」父親看著我說:「嗯,我希望你做得到。」就在那一刻,我決定不再玩裝笨的遊戲。我們會走進那些負能量的圈子,並扮演一個角色,因為說「嗯,這不適合我」很容易。這其中有一點真相,但同時你也必須說:「醒來去活吧!就像不可能失敗那樣行動。」我就是那樣做的。
你在威爾斯的工人階級家庭長大,是麵包師之子。我很難想像你認識很多藝術家或演員。成為演員這件事,對你或你的家人來說是否曾有過矛盾?
沒有。身為一個 17 歲、什麼都不懂的男孩,某件事點燃了我,然後我拿到了一所南威爾斯表演學校的獎學金。我從來沒演過戲。但我去試鏡,他們給了我獎學金。我記得去看了一齣由偉大的 Peter O’Toole 在 Bristol Old Vic 演出的戲。他在〈Look Back in Anger〉裡扮演 Jimmy Porter,而走上舞台的是一道閃電:Peter O’Toole。一個非常危險的演員。我心想,天啊,如果他走下舞台,他會走來把我們都殺了。十年後,我在 National Theater 參與 Laurence Olivier 的契訶夫〈Three Sisters〉製作中飾演 Andrei。那天演出結束有人敲門,會是誰?Peter O’Toole。這太怪了。他說:「我要你來為我做一次電影試鏡。這是一部和 Katharine Hepburn 合作的電影,叫〈The Lion in Winter〉。」
你的第一部電影。
沒錯。所以我出現並做了試鏡。他說:「你得到了這個角色。」當我偶爾回看那部電影時,我會想,這到底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是我?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這一切都在這場遊戲裡,這場被稱為生命的美好遊戲。別緊張,沒什麼大不了。沒有任何「大事」。
生命是一場遊戲、沒有「大事」這個想法,是你書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但我們究竟該認真看待什麼?什麼才重要?
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對所有事都不負責地冷漠。人生中有可怕的困難,而你必須注意它們。但最後,接近 88 歲,我每天早上醒來會說:「我還在這裡。怎麼會?」我不知道。但無論是什麼讓我還在,謝謝你!非常感激!超越我有限的自我,我能做的不多。我在年少時有一種天賦。我能背許多莎士比亞、詩之類。如今在這個年紀,我看著那些詩,它們讓我想起童年的清晰記憶,這讓我很感動。我會落淚,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曾經活過那些歲月的驚奇。我對威爾斯的清晰回憶、對父母的清晰回憶、他們的掙扎。我帶著極大的感恩回望,並有點想哭,因為我記得作為一個孩子的榮光。我有個美好的童年。我經常被霸凌。我被打過。但我回頭想,那是成長的一部分。在那些日子,老師可以對你動手。我記得曾因為我不知道某件事,被某位老師甩頭幾下。而我會做的,軍隊裡可能叫做「啞抗」。我不會回應。我只是退回自己內心,呆呆地盯著他們,這把他們氣壞了。而他們現在都已經不在了。
你贏了!
我贏了。
當你還是孩子,聽到你父親或老師說你是笨蛋,我敢說那時你自己腦中的聲音也會說:「我是笨蛋。」
沒錯。
我想很多人都在與腦中那個說我們做不到、或我們很蠢的聲音搏鬥。你是怎麼讓那個聲音安靜的?
嗯,那個聲音依然在我心裡,從童年開始。但現在它是低聲細語。我會說:「閉嘴。」所以是的,我們都有問題。我們都有侷限。但我確實相信,如果你說:「醒來去活。就像不可能失敗那樣行動,」我們其實能觸及在我們自身裡的一種力量,幫我們做到,嗯,不是所有事,但某些事。我發現我能作曲!我發現我能寫作!我透過我可愛的妻子 Stella,發現我會畫畫!
我常和演員聊,他們會說表演能滿足他們內在的某些東西。你覺得表演滿足了某種內在需要嗎?
說「需要」聽起來有點悲傷。我只是享受它。我享受學習劇本的科學般的樂趣,而我很擅長這件事。我會把我正在研究的文本的一切全學起來,因為那會重塑我內在的某些東西。我想在很深的心理層面上,我是在試著逃離我曾是什麼。
你試著逃離什麼?
嗯,那個孤獨的小孩。我從孤獨中活了下來。我挺過那些霸凌。不是說我怪他們,上帝保佑他們,甚至包括那些打我的老師。我不是受害者。如果人們選擇沉溺,好吧,請便,但你終究會死。那也是我為什麼喝酒。為了麻痺那種不舒服,不管它在我內心是什麼,因為它讓我覺得自己很大。你知道,酒很棒,因為它會讓你立刻進到另一個空間。那時的演員——Peter O’Toole、Richard Burton、所有那些人——我記得那些酗酒聚會,心想:這才是人生。我們是反叛者、局外人、我們可以慶祝。而在腦海深處還有一句:它也會要了你的命。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傢伙都走了。
你寫到你受年長演員如 Laurence Olivier 或 Katharine Hepburn 的影響,但我也好奇,這些年你與較年輕的演員合作,比如 Nicole Kidman 或 Brad Pitt 或 Ryan Gosling,有沒有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關於表演的事?
我的意思是,Brad 和你剛提到的每一位,我只有讚美。我幾年前和一位年輕演員合作,一位長得有點像 James Dean 的加拿大年輕演員。我想他覺得他就是 James Dean。我們在一起拍一場戲,我說:「我一句都聽不見你在說什麼。你為什麼喃喃自語?」我不想壞了他的心情,但我說:「如果你這樣,觀眾會走到隔壁的酒吧,因為你應該把故事說給我們聽。把聲音放大。講清楚。像後街的 Marlon Brando 那樣游移不定,不會幫到你的職涯。」之後就再也沒聽過他的消息。
在書中與你過去的訪談裡,有個一致的感覺是:表演不該被太嚴肅看待。表演對「真相」有更高的主張嗎?
沒有。它是娛樂。
你會把你拍過的任何一部電影稱為重要嗎?
不會。
一部都沒有?
沒有。
〈The Elephant Man〉?給我〈The Elephant Man〉吧!
是啊,那是一部好電影。
〈The Remains of the Day〉?〈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是,它們很好,但人們問我:「你怎麼演〈Remains of the Day〉裡的管家?」我說:「嗯,我非常安靜,非常靜止,然後安靜地走來走去。」
就這樣?
「你怎麼演 Hannibal Lecter?」嗯,我演出與他們所預期相反的東西。哦,他是個怪物?[Hopkins 用他的 Hannibal Lecter 聲音]「早安。你不是真的 F.B.I.,對吧?」你演出相反面。很容易。
我想回到書中的材料,我想聚焦的具體內容——我知道這對你很敏感。
我知道你要談什麼:我的家庭生活。
是的。
不。
即使它寫在書裡?
不。到此為止。
我可以問個一般性的問題嗎?我覺得你書裡關於你和女兒疏離的內容讓我很痛,是因為與我個人的經驗共鳴。我 20 年來大概只見過我父親兩次。那 20 年裡我和他講過一次話。我很好奇他人對那種疏離的經驗。你覺得疏離的父母與孩子之間,和解可能在哪裡?
我的妻子 Stella 寄了一封邀請來看我們。沒有任何回覆。所以我想,好吧,沒關係。我祝她好,但我不會為此白白流血。如果你想把人生浪費在怨恨裡,好吧,請便。這不在我的視野裡。我可以對過去懷恨在心,但那就是死亡。你並沒有在活。你必須承認一件事:我們不完美。我們不是聖人。我們都是罪人也是聖人,或不論我們是什麼。我們盡我們所能。人生是痛的。有時人會受傷。有時我們會受傷。但你不能那樣活。你得說,放下吧。而如果你放不下,也好,祝你好運。我沒有評斷。但我做了我能做的。就這樣。這就是我想說的一切。
你希望你女兒讀這本書嗎?
我不會回答這個。不。我不在乎。
我換個話題。
拜託。我希望你這麼做。因為我不想傷害她。
在書的結尾,你談到幾個可能套用在你身上的標籤。你說你妻子懷疑你可能有 Asperger’s【一個已不再使用的診斷】。你曾被診斷過嗎?
沒有。有人說我有所有症狀。我不知道這些代表什麼。如果我有,那我也很高興。
另一個你說可能適用的標籤是「冷漠的人」(cold fish)。而你說你比較喜歡這個標籤,而不是 Asperger’s。為什麼?
嗯,「冷漠的人」只是個說法。我不是個冷漠的人。我有很多感情。它們在我內心深處。但我不會執著於多愁善感。在這個行業,對那些我欽佩、合作過的演員,我不會產生依附。我是疏離的。我是個孤獨的人。我從來無法擺脫這點。我有相識——如果你想稱之為朋友也行。我沒有任何親密朋友。我有點疏遠。我想我有點多疑。但我不是隱士。我不住在高塔裡。我住在這裡的一棟房子,也常旅行。我有我的直系家庭,他們指揮我、告訴我該做什麼,而我也樂在其中。
當我想到你的一些我最喜歡的演出——〈Remains of the Day〉、〈84 Charing Cross Road〉、〈The Father〉、〈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或〈Shadowlands〉——那些角色都有某種情感上的疏離。那是刻意的表演策略嗎?
我想部分是刻意的。很多年前,皇家戲劇藝術學院有兩位老師,是史坦尼拉夫斯基系統的老師。我記得其中一位叫 Yat Malmgren。他是位舞蹈老師,瑞典人。我會去上他那些痛苦的肢體課。我很討厭那些課。我長得像威爾斯的橄欖球前鋒——有點壯。Yat 說:「Anthony,你有太多外向的動作能量,你會變得遲鈍。」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我本能地去發展另一面,也就是退後、待在黑暗裡、待在陰影中。這種疏離反而讓我受益,因為我不得不改變我整個心理,讓自己不要像那個衝上舞台、撞來撞去、凶猛的橄欖球員。慢慢地我學會退後。
書裡還有另一個頓悟,我想回去談談。你在 70 年代後期於洛杉磯開車,然後你感到一股拉力要你走進一座天主教堂。你走了進去,對那裡的一位年輕神父說你找到了上帝。對你來說,上帝是什麼?
那個早晨發生的事——當那個聲音說:「結束了。現在你可以開始活了,而且這一切都有其目的」——我知道那是一種遠超出我理解的力量。不在天上的雲裡,而是在這裡。我選擇稱它為上帝。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它。上帝這個詞很短。很好拼。我最近寫了一首作品,在利雅德指揮演出,是一首鋼琴與管弦樂的告別曲。【那首曲子名為「Farewell, My Love。」】而當我作曲時,我想到就是那樣。我們走了一個完整的圓,然後向下沉去,就像:「各位到此為止,這一切反正只是一場夢。」
當你愈接近那場最終的告別,你會不會從你留下的東西裡得到一點驕傲、意義或安慰?
你是說遺產?
一個傳承。
我從不去想它。當他們把泥土覆在你身上,那就結束了。我記得 Laurence Olivier 的遺孀 Joan Plowright 請我在薩塞克斯一間小教堂的靈柩旁,朗讀〈King Lear〉的最後幾句。我很震驚被邀請。那裡有 Olivier 的靈柩,滿是花圈與鮮花。之後我們上車前往火葬場。我坐在偉大演員 Maggie Smith 身旁,靈柩就在那裡,最後,當你能聽見滾輪把他送進火化爐、送進火焰時,Maggie Smith 說:「多麼戲劇化的落幕。」然後你會想,天啊,這一切到底是什麼?注入他的一生——或任何人的一生——的所有能量的驚奇。為了存活而投入的能量。看到我父親離世,我在他過世的那晚去到醫院,站在他床腳邊,我母親在撫平他的頭髮。我摸到床腳他的雙腳。那是冰冷的。他走了。而當我站在那個南威爾斯的醫院、那個寂靜之夜、那個空蕩聲響裡,一個聲音再次對我說:「你也沒多了不起。這也會發生在你身上。」
那聲音相當乾脆。
是啊,但那是某種覺醒。我們會想,對,確實如此。
Anthony 爵士,我知道我一直在繞著一個我想要你回答的問題。你認為你的人生有意義嗎?
我能給它的唯一意義是:我所追尋、所渴望的一切找到了我。不是我找到它。是它來到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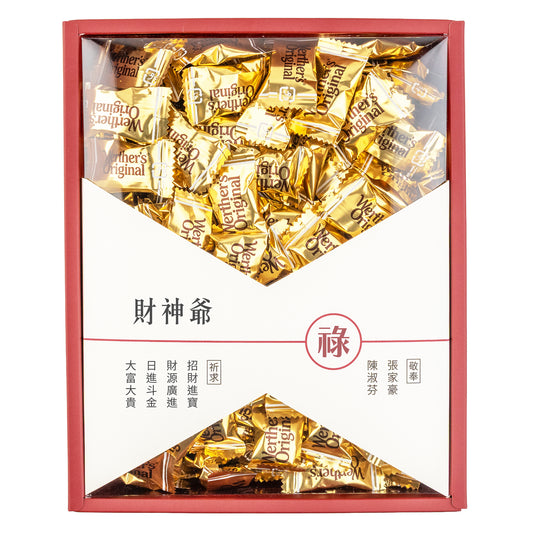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