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鼓勵生育計畫:三十年後仍未見成果
Share
日本已經嘗試提高生育率30年。現在,其他富裕國家也在效仿。
1989年,日本看似是一個勢不可擋的經濟超級大國。其企業超越了競爭對手,並購買了洛克菲勒中心等美國標誌性產業。然而,在國內,政府已經察覺到一場逐漸醞釀的危機:生育率跌至歷史新低。政策制定者將其稱為「1.57震撼」,指的是女性在育齡期間預計平均生育的子女數。
他們警告說,如果出生率繼續下降,後果將是災難性的。稅收將上漲或社會保障金縮水,日本的孩子將缺乏足夠的同伴互動,隨著年輕勞動力的減少,社會將失去活力。是時候採取行動了。
從1990年代開始,日本逐步推出旨在促使人們多生孩子的政策和宣告。政府要求僱主提供最多一年育嬰假,開設更多補貼托兒名額,呼籲男性做家務並休育嬰假,並要求公司縮短工時。1992年,政府開始對擁有一個孩子的家庭直接發放現金津貼(在此之前,僅針對第三個孩子),後來還推出了針對所有子女的雙月津貼。
然而,這些措施並未奏效。去年,日本的生育率為1.2。在東京,這一數字甚至低於1。去年,日本出生的嬰兒數量降至政府自1899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現在,其他發達國家越來越像日本。根據2019年聯合國人口基金的一份報告,全球有一半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即每位婦女生育2.1個孩子——的國家。
為何在氣候變遷、核災風險增高、人工智慧接管工作的前景下,各國仍要關心人口縮減問題?在全球層面上,人口並不缺少。然而,過低的出生率會給某些國家帶來問題。
聯合國報告的作者之一、維也納人口研究所副主任托馬斯·索博特卡用簡單的計算來說明這一點:在擁有全球最低出生率(每位婦女僅生育0.72個孩子)的南韓,1970年約有100萬嬰兒誕生,而去年僅有23萬人。當然,簡單地說2023年出生的每個人都需在其黃金工作年養活四位退休者未免過於簡化。但如果沒有大規模移民的情況,「對南韓社會而言,這問題將非常難以組織和解決,」索博特卡表示。
從義大利到美國,類似的擔憂也存在:工作年齡人口數量被老年人數超過;小鎮人去樓空;重要工作職位無法填補;商業創新陷入停滯。移民或許是一個直接的解藥,但在許多出生率下降的國家,接受大量移民已變得政治上無法接受。
在歐洲、東亞和北美,許多政府正像日本一樣引入有薪父母假、托兒津貼和直接現金補助等措施。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刻意針對生育率的國家數量從1986年的19個增加到2015年的55個。
這一話題已出現在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D.范斯批評該國低出生率,並為他過去關於「沒有孩子的貓女士掌控國家」的言論辯護。范斯提出增加兒童稅收抵免,並表示他會考慮像匈牙利那樣的政策,讓多子女的女性享有較低的稅率。民主黨方面,卡馬拉·哈里斯提議對有嬰兒的家庭提供6,000美元的稅收抵免。儘管哈里斯並未將此作為促進生育的政策,但它與其他國家正在做的事情不謀而合。
倡導者有時會認為,如果提供有薪家庭假或免費托兒服務,出生率將神奇地上升。但30多年來,日本實際上是這些舉措的實驗室——研究顯示,即便是慷慨的政策,也只能帶來些微的增長。
經過多年的政治豪言壯語和政府措施不斷增加,現代家庭似乎還是不想擴大規模。「要讓人們改變偏好,這些政策就必須非常、非常具有強制性,」索博特卡表示。「或者要讓他們生育本不想要或計劃中的孩子。」那麼究竟什麼樣的措施才能真正促使人們多生育孩子?如果什麼措施都無法奏效,原因又是什麼?
大規模的生育下降
有大量證據表明,政府可以改變生育率,但通常是往一個方向:下降。
在東亞,許多如今生育率極低的國家最初是自己造成這一現象的。中國實行了一胎政策長達30多年。二戰後,日本鼓勵廣泛使用避孕措施,並為了減少人口而將墮胎合法化。同樣地,南韓政府在1970年代初期將墮胎合法化,並不鼓勵家庭生育超過兩個孩子。
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經濟學副教授閔哲·楊研究南韓生育率問題時提到,他的母親告訴他「如果你帶著超過兩個孩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這會是一種社會污名」。
在歐洲和美國,隨著越來越多女性進入職場,宗教影響力——尤其是天主教——減弱,生育率也隨之下降。年輕人開始離開他們成長的社區,追求職業生涯並建立推遲結婚的網絡,這導致開始生育的年齡也更晚,子女數量減少。
較低的生育率意味著進步:嬰兒死亡率下降減少了人們需要生育多個孩子的必要性。隨著經濟從以農業為主或家庭擁有的企業轉型,人們專注於休閒和其他抱負。女性則可以追求職業目標和撫養子女以外的個人成就。這一切的基礎是避孕措施的普及,使女性能決定是否以及何時懷孕。
然而,擁有多個孩子的障礙也越來越多。房價飆升、零工經濟讓年輕人擔憂自己的財務穩定性,甚至是未來子女的財務安全。教育孩子並讓他們為越發競爭且不公平的職場做好準備的成本不斷上升。曾幫助人們找到未來伴侶的機構,如教堂或正式的婚姻介紹服務,也逐漸消失。
隨著家庭子女數減少,他們在現有子女上投入更多精力。在中國、日本和南韓,父母競相將子女送進最好的學校,並從小就支付嚴格的輔導費用。這些現象在美國也越來越常見。8月,美國衛生部長維韋克·穆爾西發布公告,呼籲關注美國父母壓力和心理健康問題上升的情況。
根據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譚寶林的說法,子女不再通過其勞動提供直接的經濟價值,也不像過去那樣能保證在父母年老時照顧他們。「我們目前處於一種養育子女完全是為了純粹的快樂和偏好的地步,你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並在休閒和職業發展上作出一些犧牲,」譚說。
更好的爸爸,更多的嬰兒?
儘管家庭和工作生活發生了變化,但關於誰應照顧孩子的傳統觀念——當然是女性——對政策規定仍頑強抵抗。「文化上的期望設計來適應已經不復存在的生活方式,」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家馬蒂亞斯·多普克說。「這是富裕國家極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在日本,那種源於許多女性留守家庭的時代的嚴苛工作文化,使得平衡事業和家庭變得困難。儘管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員工仍被期望長時間工作,晚上與同事或客戶應酬,並頻繁出差。與西方相比,日本母親,即使是有職業的母親,仍要負擔大部分的育兒和家務。
東京專修大學社會學家和性別學者根本久美子訪問了28名在管理或行政職位上的日本女性。她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子女。而那些有子女的人則要麼依賴父母幫忙,要麼每月花費高達2,000美元的育兒費。「幾乎所有這些女性都表示她們的丈夫沒有幫助她們,」根本表示。
世界另一端的一些政府試圖解決這些不平等現象。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制定了政策,旨在將一些責任轉移到男性身上,以支持更多的家庭。
1995年,瑞典推出了被稱為「爸爸月」的政策,這是一個月的育嬰假,專為尚未在孩子出生後休育嬰假的配偶——通常是父親——而設。如果這位配偶不休假,這對夫婦將失去這個月的假期。隨著隨後幾年中「用或失去」的第二個和第三個月的增加,越來越多的父親休育嬰假。「這改變了對好父親的文化期望,」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員伊娃·莫伯格表示。
然而,瑞典的生育率並未上升。經濟學家們認為,這並不意味著政策失敗,因為瑞典的生育率仍高於東亞。「對經濟學家而言,問題在於即使生育率沒有上升,它也可能下降得更低,」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安娜·勞特說。
一些保守派和宗教學者認為,與其鼓勵父親多承擔責任,政府應該激勵女性退出工作養育子女。但即使是那些提供慷慨福利的國家,比如芬蘭和匈牙利,讓父母在孩子出生後休兩到三年假,也未看到顯著的生育率增長。
婚姻,或是更根本的問題
如果家長之間更多的性別平等、稅收減免和現金津貼都無法創造更大的家庭,那麼處於絕望的政府還能做些什麼?
在日本,政策制定者正嘗試一個新策略:促進結婚。去年,日本結婚的夫婦不到50萬對,是自193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儘管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單身男女都希望結婚。障礙之一是許多年輕人與父母同住——根據2016年的數據,20至39歲人群中有近40%與父母同住(這是目前可用的最新數據)。「與媽媽同住不是找到終生伴侶的最佳浪漫環境,」弗吉尼亞夏洛特斯維爾家庭研究所生育推廣計劃主任萊曼·斯通說道。
日本政界人士也討論了提高工資的重要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應支持公司社交活動,這些活動可能促成關係。LGBTQ倡導者則認為,日本應該合法化同性婚姻,並幫助這類伴侶養育子女。
東京都政府最近推出了自己的交友應用程式,但並未公佈任何註冊數據。在社交媒體上,這一舉措似乎受到馬斯克的關注比當地居民更多。
很難想像這次推動結婚的努力會比日本過去三十年來的各種舉措更能提升出生率。最終看來,政府只能做到這麼多。
在中國,政府鼓勵生育的強勢行為已引發反彈。在民主國家,任何帶有強制意味的政策也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對。事實是,是否生育這樣重大的決定,很少僅僅取決於經濟因素或誰來換尿布。
影響這些選擇可能超出了傳統政府政策的能力範圍。對於大多數富裕國家的人而言,生育是非常個人化的選擇,觸及到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社區以及我們對未來的看法。有時候,也與運氣有關。「政策無法在合適的時間找到你夢想中的最佳伴侶,」索博特卡指出。
這並不是說為促進出生率而實施的一些政策(或至少部分為此目的)沒有意義。提供高質量的補貼托兒服務、鼓勵父親參與孩子的生活,以及重塑工作場所以便員工能與家庭互動,這些措施都能幫助提高那些有孩子的人的生活質量。
在東京,許多有小孩的朋友對美好且負擔得起的托兒所讚不絕口,這些托兒所讓從幼兒到5歲的孩子吃上營養午餐,並由照顧者每天發送照片和個性化更新信息。與我在1980年代末作為報社實習生在這裡的時候相比,我看到更多的父親在周末帶著孩子乘坐地鐵或到公園玩耍。
但仍難以逃避老年人口遠遠多於嬰兒的感覺。而且,我告訴你,比起看到父母帶著小孩,我更常看到的景象是成年人帶著穿毛衣和靴子的狗,將狗裝在胸前背帶裡或推著狗坐在嬰兒車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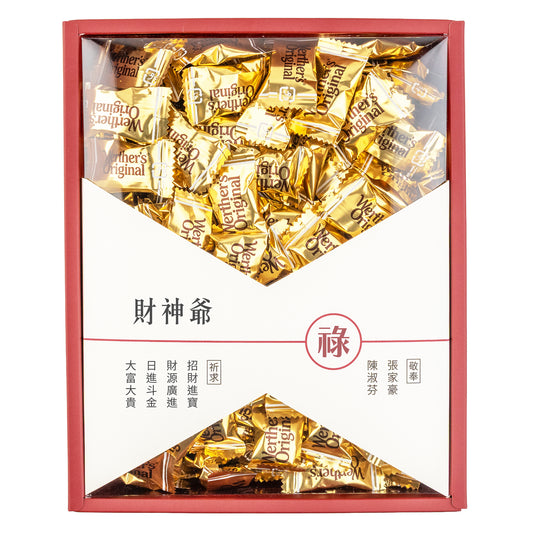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