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絕望不是終點:告別假希望,看清現實,重新繪製人生出路。
Share
希望是不可或缺的。但當虛假的希望讓我們看不清現實時,一小段短暫的絕望,反而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解藥。
我們這個物種擁有非凡的能力,可以想像未來。雖然鳥類、蜜蜂、老鼠和其他動物也會為自己的生活可能走向做決定——例如要去哪裡覓食、要走哪一條路——但人類的未來思考方式有所不同。我們的選項極為廣泛,我們的計畫層層堆疊且複雜,我們的視野可以延伸數十年,甚至數個世紀。
我們可能會夢想減少地球海洋中的塑膠汙染、成為一名甜點師傅、從其他國家領養孩子,或是為社會正義而工作。這些都不是直線式、單純的目標。我們每一個投入其中的大型人生計畫,都包含無數可能的行動路徑,而我們持續在建構、更新與修正這些路徑,較小的子目標又一層層嵌套在更大的目標之中。當我們為了那遙遠的回報精心繪製複雜路線時,也將大量心力與情感投注在那些被想像出的未來之上。正因如此,當我們一再碰壁,看著精心搭建的未來開始崩解時,希望很容易就會轉為絕望。在那樣的時刻,我們會銳利而沈重地意識到:自己曾經夢想過的某個未來,可能正在消失。
這種經驗可能是毀滅性的。也因此,絕望常被描繪成一種破壞性的心態,讓我們困在自我挫敗的循環裡,或逼得我們太早放棄。在最糟的情況下,它甚至可能驅動各種「孤注一擲」的行為。當絕望揮之不去,或一次又一次回來時,會助長自殺意念、成癮、慢性失眠以及其他嚴重的傷害。經濟學家 Anne Case 與 Angus Deaton 甚至創造了「絕望之死」這個說法,用來描述在日益疏離且不穩定的社會條件下,美國工人階級自殺、藥物過量與酒精相關死亡人數的上升。
考量到絕望可能帶來的種種毀壞,我們或許會以為,最好能永遠不要感到絕望才對。但絕望有時也能帶來幫助嗎?正如一些學者與行動者開始指出的,如果我們缺乏感受這種情緒的能力,或許就會少了一種必要的清晰感,讓我們懂得放棄失敗的追求,並找到新的方向。短暫地與絕望相遇,有時反而會帶來澄清,讓我們更嚴肅地檢視自己正走向何方。或許,唯有經歷這種痛苦的感受,我們才得以開始從頭校準未來的艱難工作。
絕望是一種強烈的情緒,正因為它宣告了一個我們極度重視的目標遭到徹底挫敗。那是痛苦地認知到:在我們內在的未來地圖上,一條值得追尋的路徑已經失落。想像一位學生得知自己拿不到原本指望、用來完成學位的獎學金。她所想像的未來——明年走上畢業典禮舞台——突然之間彷彿整個塌陷。
依據哲學家 Anthony Steinbock 的看法,絕望常被視為「對希望最深刻的挑戰」,因為它會立刻扼殺希望所倚賴的那些活動:面向未來的想像、規劃,以及採取具體行動來推進我們渴望的結果。絕望奪走了我們想像可行前路的能力。留下的,不只是挫折或憤怒,而是更沉重的東西:一種未來正在關上、無論多努力都無法扭轉局勢的感覺。
希望的確可以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懷抱希望本身,也潛藏著風險。
正如醫師 Randolph Nesse 所說,希望與絕望是「在慾望之舞中內在緊密交纏的夥伴……」。我們會隨著自己對成功機率的判讀,在兩者之間來回擺盪。希望是一種情緒訊號,表示目標仍在可觸及的範圍之內——提醒我們應該持續規劃、推進,甚至堅持朝夢想前進。相比之下,絕望則是前景黯淡的訊號。它告訴我們,也許是時候抽身、放手,重新考量其他選項。近年來,聚光燈大多打在希望身上。哲學家強調,希望在賦予我們毅力與韌性、讓我們得以朝困難目標奮鬥方面具有核心地位。大眾寫作者也呼應此點,將希望描繪成航行於不確定未來時的重要資源——例如 Jamil Zaki 的《Hope for Cynics》(2024)、William R Miller 的《8 Ways to Hope》(2024),以及 Sumit Paul-Choudhury 的《The Bright Side》(2025)等書。希望的確可以是一股必不可少的力量,支撐我們最雄心勃勃的計畫,並讓我們「看見」那些值得嚮往的未來仍然可達成。但懷抱希望,同時也存在風險。
在近年對希望的大肆讚頌之旁,學者與行動者也開始揭開絕望隱藏的優點。與希望不同,絕望有可能保護我們免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引導我們轉向更可行的目標。面對氣候危機,有些行動者甚至乾脆完全轉身離開希望。哲學家 Jakob Huber 在〈Hope from Despair〉(2022)一文中指出,像 Extinction Rebellion 這類激進的氣候行動團體,已經轉向「較陰暗的態度,如憤怒、恐慌或恐懼,甚至,也許最令人意外的,是絕望」。有些人甚至呼籲,讓希望「死去」。為什麼一群致力於打造更好未來的人,會呼籲讓希望死亡呢?
正如 Huber 所觀察到的,希望會讓我們緊抓著令人感到安慰的幻象不放,使我們看不見證據,並關上那些更為現實的替代方案。氣候危機,正好提供了一整套特別鮮明的危險希望樣本。想想「科技解決萬事」的信念——也就是認為光靠科技就能解決人類最嚴峻挑戰的想法。在氣候危機脈絡下,這種觀點暗示,只要有科技來拯救我們,就毋須改變既有的生活方式。
與之密切相關的,還有地球工程,這種構想承諾,只要部署各種捕捉並儲存排放的創新技術,我們就能維持目前高度仰賴碳排的生活方式——儘管實驗性計畫所顯示的儲存容量,與問題的龐大規模相比幾乎微不足道。與此同時,「經濟重返成長」這種充滿希望的神話仍在政治光譜上各方持續流傳,忽視了不斷累積的債務,以及在一顆有限的星球上追求無限擴張,在熱力學上根本不可能。走到最極端時,我們會看到終極逃避式的希望:超級富有的生存主義者投資豪華地堡,或是幻想拋下地球、前往其他星球殖民。所有這些希望都有一條共同線索:它們讓我們得以逃避面對自己當前軌跡中那些令人不適的真相。一劑令人清醒的絕望,會不會其實是對抗虛假希望與誘惑幻象的有效解毒劑?
對於像我們這樣以未來為導向的存在而言,擁有一種情緒來提醒自己必須放棄失敗的路徑,可能和另一種推動我們在不確定但值得追求的目標上持續前進的情緒,同樣重要。放下一個珍視的計畫,往往意味著必須拆解整個由想像可能性編織而成的網——一整張夢想的網。當希望讓我們緊緊抓住這些投射時,絕望則能提供所需的心理距離,讓我們得以重新評估與調整。絕望賦予我們那份看清局勢的清明,甚至是勇氣,去承認局面已經逆轉。它告訴我們,要從不再符合自身利益的追求中抽身而退。若沒有這種不適與悲傷,我們可能就會錯過那個開始重新繪製內在路線圖的訊號。正是透過絕望,我們才得以真正感受到某個未來正從手中滑落的全部重量。
各種形式的悲傷,都在我們經歷失去之後,協助我們調整自己的信念與期待。心理學家 Melissa Karnaze 與 Linda Levine 就曾形容悲傷是「認知改變的建築師」,因為這種感受能幫助人們記錄損失,並理解全新的現實。同樣地,絕望也可能給予我們重新洗牌未來「地圖」的衝動,當某條路徑被關閉之後尤其如此。它透過把我們拉回當下、暫時中止那不斷奔向未來的想像活動,來達成這件事,讓我們消化這個失去的意義,並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走。這個認知重置的片刻,就是設計更可行未來的第一步。
如果短暫的絕望能幫助我們放下那些再也不可能實現的未來,它同時也會為新願景的形成騰出空間。這些新願景讓我們有機會想像更腳踏實地的未來圖像。以氣候危機為例,這並不是指各種科技修補、逃離的幻想,或其他光鮮亮麗的希望,而是指緩慢扎實的工作:打造更穩健的願景,讓它們更深植於我們所居之地,以及支撐我們的各種關係之中。在絕望之後,輪到希望出場——不是去幻想無邊無際的未來,而是去想像一條條更可居住、更可走下去的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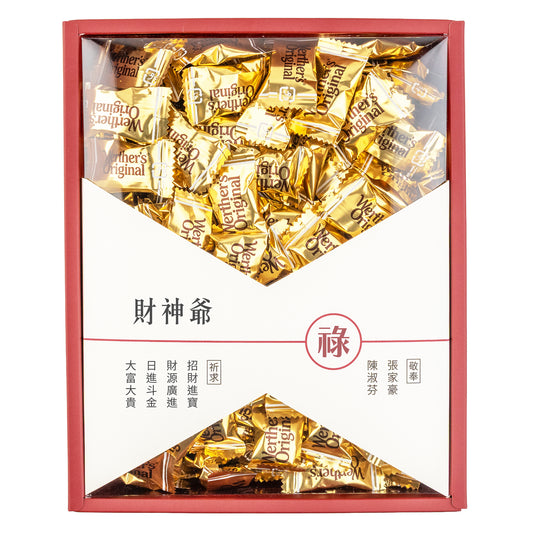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