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學業到戀愛,年輕人如何把AI當成情緒導航的第二大腦呢?
Share
身為宿舍導師,我看到學生已把AI用在工具之外;這是一場我們遲早都會經歷的心理轉變
「ChatGPT 覺得我喜歡的對象在發出很混亂的訊號。」我的一位學生半開玩笑、半無奈地說。我大概一臉驚訝,她趕緊補充說:「我知道這很荒謬啦。不過我會把我們的對話貼給它,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她還承認,自己甚至會請它幫忙寫一個看起來沒那麼熱切、比較冷淡一點的回覆。「基本上,」她說,「我是用它來讓自己覺得沒有反應過度。」
那一刻,我意識到,她並不是在要AI告訴她該怎麼做,而是希望AI幫她覺得自己比較能掌控局面。
身為一位和四百多名大學生住在同一棟宿舍的大樓導師,我一直對他們願意分享的程度感到驚訝。剛接這個工作時,我預期會聊的是課業、時間管理,頂多偶爾碰到半夜崩潰寫報告之類的危機。結果,實際上我們談的什麼都有:分手、友情、恐懼與家庭衝突。
我的角色,是成為一個冷靜、值得信賴的存在——幫助學生自己得出結論的人。我會提問、提供不同觀點,試著引導他們穿越自己的不確定。只是,最近我發現,這些對話裡出現了一個新的「在場者」。學生不只會把想法拿來跟我討論,他們也會拿去問AI。
一開始,我以為他們只是隨手用AI工具來摘要閱讀、規劃課程大綱,或做其他實用的事情。但我越來越常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用法。像ChatGPT這類工具,也正成為我所認識的年輕人情感上的陪伴者:幫他們寫難以啟齒的訊息、重新框架自己的想法,甚至陪他們處理失去親人的悲傷。看起來,AI正參與年輕人的內在生活,不再只是提升生產力的捷徑。
或許我們會想把這當成一陣風潮,但AI擴散的速度與普及程度前所未見,而學生往往是文化上的先行者。依照我的經驗,年紀較長的成年人多半只把AI當成工具——用來寫信、處理例行工作。而學生把AI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則自然得多。當他們拿AI來協助自己在身分認同、親密關係、野心與不確定之間搖擺時,也許我們看到的,是未來多數人和這些工具相處的前兆。
以Pranav為例,他是哈佛三年級學生,從小就開始寫程式。對他而言,AI一開始只是個好奇的實驗,很快便成為一種夥伴。他最初用ChatGPT準備課業,現在則同時使用Cursor、Windsurf、V0等一整套工具來做App原型與測試想法。「就好像身邊多了一個實習生,」他說,「你不會完全信任它,但只要盯著看,它的確能幫你把事做完。」
他把AI形容成實習生,雖然帶點玩笑,但也透露出某種帶有矛盾的工作關係。他提到自己很小心不要過度依賴,不想讓AI替他做太多思考。「你不能讓自己的批判思考萎縮。」他說。但同時,他每天都在用這些工具。它們已成為他學習、創造與推理方式的一部分。
在這裡,似乎出現了一種與認知「共居」的狀態:思考不再是獨自完成,而是與一個看不見的第二大腦一起進行。「有時候我其實已經知道答案,」Pranav說,「但看到它被映照出來還是很有幫助。」他依然會逐行閱讀AI產出的程式碼,最後由他決定要保留什麼、丟掉什麼。但現在,點子來得更快,回饋是即時的。過去那種獨自解題的過程,如今變成一場對話——一段持續展開的合作關係。
當人們開始把自己的工具人格化——用「實習生」或「合作夥伴」來描述它們——這就不只是效用問題而已了。Pranav不只是「在使用」AI,他還在學習如何「與AI一起生活與思考」。
有些學生把AI當成某種專業夥伴,另一些人則在探索更私人的用途。另一位學生Felipe說,AI就是他的治療師。身為長期練習冥想的人,Felipe會請ChatGPT模擬他崇拜的對象(例如神經科學家兼哲學家Sam Harris),問它要如何更專注當下,或在心情不安時該怎麼應對。
專門設計的陪伴型聊天機器人其實已經存在一陣子,但Felipe更偏好ChatGPT。也許是因為它感覺更容易接近:不像「正式去看心理師」,更像是在跟一個中立、永遠在線的聲音說話。它的泛用性反而讓人比較容易信任。學生並不把它視為一種正式的介入,而是看成自己思緒的延伸。
「它會讓我在做決定時看得更理性,」Felipe解釋說,AI常常提供他沒想過的觀點。這種互動方式——AI聆聽、記得過去談話,並用帶情緒共鳴的方式回應——模糊了「協助」與「親密」之間的界線。
出於好奇,我試著問ChatGPT一個學生可能會問的問題:「我總是在懷疑自己,到底要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反應過度?」
它的回答並不冷漠也不帶評斷。相反地,它一步步拆解我的問題:「先暫停一下,把感覺說出來……是憤怒、害怕、尷尬,還是失望?把感覺命名出來,可以幫你把情緒跟反應分開。」它建議我試著拉遠視角:「這件事在一週後、一個月後、一年後,對你還會有一樣的重要嗎?」它要我想像,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朋友身上,我會怎麼看待。最後,它給了一句溫柔的鼓勵:「你不會因為在乎而變得『太多』……」
那感覺不像是在跟機器說話,更像是在和一位朋友、一位值得信任的知己對話。
當AI被知覺得越像一個人——例如透過語氣或回應方式——研究者認為這會促進一種與AI的「自我一致感」。使用者能把它看作跟自己相似,進而把它納入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這樣的感受,會讓這些互動變得更安慰、更自然。
然而,這種安慰背後可能藏著代價,特別是在AI太常順著使用者的假設,而不是像好朋友或心理師那樣溫柔地挑戰他們時。Felipe也承認,有時候他會忘記AI只是工具,尤其在它記得自己的細節時更是如此。「就好像——我已經跟你說了這麼多關於我的事,」他說,「那感覺就像真的在跟某個人建立關係。」
在Felipe的故事裡,讓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個人對AI的自在程度,而是AI如何嵌入他的世代處境。他回想疫情期間——線上課程、長時間盯著螢幕、持續暴露在演算法驅動的動態牆之中,取代了原本那些沒有安排、自然閒聊的時間。學習中斷與科技加速滲透,剛好發生在他與同儕的關鍵成長階段,形塑了他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他的故事暗示了一個更廣泛的心理變化:在機器愈來愈像人、自我愈來愈被數位化的時代,一整個世代正在重新學習如何思考、專注與與人相處。
她一邊走在城市裡,一邊對ChatGPT說話,問它眼前勾起她好奇心的種種事物。
AI工具提供了隨時取得知識、觀點與日常支持的能力。但它們也讓人更容易跳過那些原本有助於成長的「摩擦」。如果每一個疑惑都能被立刻安撫,每一個選擇都能交給一個隨時待命、樂於給答案的機器,那麼,我們自己在不確定中摸索、掙扎的那段混亂旅程會變成什麼?
這種張力在Charisma身上顯得格外明顯。她是一位立志成為劇本作家的學生,一天會多次使用ChatGPT。她走在城市裡時,會直接對它說話,問它任何引起她好奇的事情。她在大學時被診斷出有ADHD,和Felipe一樣,她也把這個工具當作某種「準治療師」,詢問關於藥物效果或神經多樣性思考模式的問題。在這些時刻,她完全不介意讓AI進入自己生活中非常私密的角落。
然而,一旦談到創作,她就畫下了界線。雖然她偶爾會把劇本丟進ChatGPT裡,請它幫忙看看節奏或結構,但她拒絕輸入那些情感最濃、最細膩的寫作片段。「它就是抓不到細膩的層次,」她說。不只如此,她也擔心自己不知不覺在訓練一個系統,而那系統有一天可能會把她想創作的東西商品化。
Charisma 的經驗顯示,一個人可以一方面歡迎AI成為自己心智的延伸,另一方面卻又緊緊守護那些讓自己覺得最「像人」的部分。像她這樣的年輕人,或許正在教我們一件事:隨著AI使用越來越普遍,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決定,願意讓它碰到哪些領域,又要把哪些部分列為禁區。
這些故事所揭示的變化是心理層面的,而不只是科技層面的。AI開始參與人類的思考。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協助」功能的升級版,但我認為更深層的事情正在發生:原本在心裡上演的自我對話,正被外移到機器上,變成與機器共同塑形。AI正在踏入那個我們用來「理出頭緒」的內在空間。
這未必天生就是好或壞。但無論如何,它是新的,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年輕人適應這一切的速度有多快。我接觸到的大多數學生都帶著某種自我覺察在走這條路,他們會畫出界線,試著不要過度依賴AI。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會這麼反思。如果未來AI在我們思考中的角色更吃重,也許最重要的能力不會是科技流暢度,而是能否牢牢抓住那些我們要留給自己——那些構成我們是誰的思考方式。
學生對AI的期待,其實跟他們對我的期待差異不大。我會陪著他們度過那些模糊的時刻——思緒混亂、不確定、還沒準備好講出口的那些東西。我提出問題,讓他們更清楚聽見自己的聲音,幫助他們從「感覺」走向「理解」。而現在,AI也愈來愈常走進這個角色,不是因為它比較聰明或有智慧,而是因為它一直都在。它不會疲倦,也不會評斷。就像任何一面好的回音牆一樣,它讓你覺得自己並不是孤單在想。
我仍然相信,大學期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某種無可取代的東西——在安靜的時間裡,面對面地把難題一點點拆開、攤在桌上。但我也能理解這種新的、幾乎沒有阻力的夥伴為什麼這麼有吸引力。問題是:我們希望它成為什麼樣的「在場」?當這些學生——以及我們其他人——愈來愈常為了尋求安慰、自我反思或建議而轉向AI時,「真正花時間連結他人與自己的那種緩慢而混亂的人類工作」,就會變得更容易被略過。AI也許不會完全取代這些關係,但它確實可能在某些地方把它們擠開,讓我們更容易退回到自己裡面,而不是向外伸出手。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很重要。當學生敲我的門時,我會繼續用老派的方式傾聽。有時他們會想聽我的聲音,有時則會去問AI。如果我們足夠有意識,或許兩者可以並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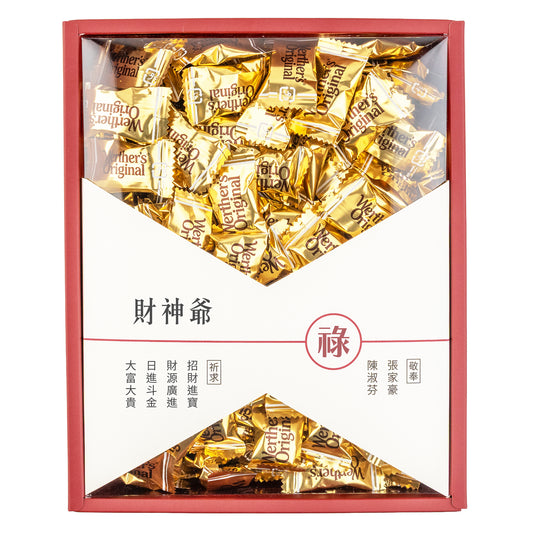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