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凍卵:追求身體自主與時間自由
Share
我看著超音波螢幕,婦產科醫師在數我卵巢裡的卵泡,那些卵泡就像 NASA 影像中的黑洞。我體內有超過 30 個卵泡,這景象讓我不安。醫生看起來很興奮,「這些卵巢看起來真是豐滿啊!」她說。
她的評論讓我回到現實,我不再是神秘的銀河現象的所在地。
我即將成為少數選擇凍卵的美國拉丁裔女性之一,這是一種叫做卵子冷凍保存的生育保護程序。拉丁裔女性的凍卵率是最低的之一,部分原因是這個程序的成本昂貴,每次循環可以高達 15,000 美元。拉丁裔女性是美國最不被保險涵蓋的群體之一,且工資普遍較低。
還有一個迷思是拉丁裔女性生育能力旺盛。這種種族主義觀念剝奪了我們,導致 20 世紀大量針對拉丁裔女性的強制絕育行動。我們拉丁裔女性之間也常自以為生孩子容易,連我們的醫生也是這樣認為。因此,西班牙裔女性進行不孕症檢測的機率低於白人女性,接受不孕症治療的比例也較低。但拉丁裔女性和其他女性一樣難以懷孕。事實上,有些研究顯示,有色人種女性比白人女性更容易面臨不孕問題,且治療結果也較差。拉丁裔女性的生育率確實高於其他女性,但這是由於避孕措施的不平等獲得以及文化差異等因素,比如認為沒有小孩的人生不會快樂,特別是在外來的拉丁裔中尤為普遍。
35 歲時,我面臨來自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家族女長輩們越來越大的壓力,她們希望我生孩子。「妳會落得孤單一人。」一位阿姨在節日派對上大聲說。我母親在我父親開始吸毒後獨自撫養我和姐姐,她反覆對我因前男友酗酒問題而分手的決定感到遺憾。「沒有人是完美的。」她說,「妳本來可以先生個小孩,再離開他。」
我的家人擔心我會成為他們曾經害怕的幽靈,那曾促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匆忙與不可靠的男人生育——成為無子的女士,成為獨身的老太太。在我職業生涯達到巔峰之際,成為全國專欄作家,我正處在成為家族失敗者的邊緣。
通過凍卵,我希望能從親戚們的壓力中解脫,給自己更多時間找到符合我標準的伴侶。但在生育診所,我又遇到新的焦慮源。醫生告訴我,我的卵泡數量超過 30 個,這對於我這個年紀的女性來說是很高的。我的卵巢狀況非常適合進行凍卵,但我需要服用荷爾蒙來刺激卵泡過度生長。
從小到大,我一直在逼我的身體「過度生產」:成績單上的全優成績、禮貌的微笑和問候、優秀的班級行為獎、拼字比賽獎杯、大學學位、獲獎的新聞報導、備受好評的書籍,面對仇恨和騷擾時保持冷靜和同情心。我的價值在於產出。我不得不將身體裡的養分榨乾,就像工業榨乾土地一樣。
近年來,各種族群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因為我們為了追求更高的教育或其他抱負而推遲生育,但拉丁裔女性的生育率下降最為顯著。許多拉丁裔女性不願在高生活成本和缺乏帶薪育嬰假的情況下生孩子,有些女性則乾脆不想要孩子。
但在這個國家的神話中,拉丁裔存在的意義就是生產。我們占了服務業的三分之一,是美國經濟的支柱。當無數同胞詆毀我們的勞動,聲稱我們在奪走他們的工作或取代他們時,我們必須繼續清掃他們的旅館、建造他們的房屋、為他們服務。而這一切,我們得到的報酬還不到白人男性的 60%。由於母親的犧牲,第一代和第二代拉丁裔女性得以獲得文化或經濟上的權力,但我們無法擺脫不穩定的感覺,並經常與焦慮、身體疼痛等症狀鬥爭。
30 多歲的時候,我的免疫系統變得過度活躍,攻擊甲狀腺和其他器官,我開始出現反覆的疲勞和肌肉疼痛。我母親患有狼瘡,一種慢性自身免疫疾病,這種疾病對拉丁裔女性的影響尤為嚴重,其症狀可以由壓力觸發。我的家庭中有許多女性都有自體免疫的問題。在我同時處理醫生的約診、工作期限和糟糕的約會之際,我也擔心自己會走上一條造成永久健康問題的道路。我想成為母親,但我需要休息。
幾年前,一位白人朋友告訴我,凍卵讓她釋放了大量壓力。因為不再需要把大部分的空閒時間都投入到約會中,她可以去度假,甚至小憩。
我開始幻想凍卵。這很昂貴,但我的朋友的公司支付了她大部分的費用。可惜的是,儘管我的保險計劃涵蓋了一些費用,但大部分程序的花費仍需由我支付。這會耗掉我大部分的積蓄。不過,能夠有保險覆蓋,我已經很幸運了。
儘管大型公司,特別是矽谷的公司,對凍卵的覆蓋率有所增加,但拉丁裔在這些工作中嚴重不足。
有些人找到克服經濟障礙的創意方法,例如在費用較低的國家進行這項程序。38 歲的邁阿密博物館策展人 Jennifer Inacio 告訴我,她在巴西凍了卵,花費約 6,000 美元,而且她相信自己在那裡得到的照顧比在這裡更好。每當她有問題時,她只需簡訊給她的醫生,醫生會立即回覆她。「這讓我感覺很安心。」她說。
住在洛杉磯的 38 歲時尚設計師 Brenda Equihua 考慮在墨西哥蒂華納凍卵,但她希望能有心安,將卵子儲存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她通過個人貸款負擔得起洛杉磯的治療,並通過在蒂華納購買一些藥物來減少費用。「我覺得這次經歷讓我感到很有力量。」她說。
凍卵的朋友也形容這個程序讓她感到有力量,但我害怕針頭,更害怕在我需要休息的時候,讓身體進一步超量生產。
但我的選擇是什麼呢?要麼錯失成為母親的機會,要麼重蹈家庭覆轍,和問題伴侶生育,接著扮演母親與父親的雙重角色,並持續擔任其他工作,度過一生。
我決定進行這個程序。它會痛苦,甚至可能會懲罰我,但我會奪回我休息的權利。
我將針刺進我的肚子,試圖穩住我的手,將含有促卵泡激素的 Gonal-F 注入體內。我能感受到針刺穿皮膚,因為我的手一直在顫抖。我抽出針頭並過快地鬆開活塞,導致血液和一種黃黃的物質——脂肪?——流入針筒。血滴下我的肚子。
這是我開始注射以來的第三次事故。首先,我刺錯了肚子的部分,接著一位想幫忙的朋友將昂貴的藥物噴到地板上。現在又這樣。
在我即將開始凍卵的幾天前,我失業了。而我的卵泡數量急劇下降。我考慮推遲程序,給我的卵巢再次「超常發揮」的機會。但最終,我決定在失去健康保險和勇氣花費大筆錢之前進行這個程序。
一開始,我每晚要給自己注射兩種藥物,並吞服第三種藥片,這些都是為了在體內引發高濃度荷爾蒙,促使卵泡生長。幾天後,我還得加入第三種注射,以阻止身體排卵的衝動。
每隔一天,我都要去診所測量卵泡。它們越來越圓潤飽滿,我試著不把它們當作黑洞,而是把它們想像成通往新生命的神奇之門。其中一個卵泡膨脹得比其他的快。我告訴自己她將來會是一個小女孩,和我一樣野心勃勃。我確保自己吃健康的食物來滋養這支「卵子大軍」。在尋找新工作和寫第三本書的提案之際,我告訴自己不要緊張,因為這可能會對卵子有害。
但注射讓我情緒化、頭昏、疲憊。我被告知不能運動,因為這可能會導致輸卵管扭轉;隨著日子的推移,我越來越焦慮。我的卵巢又重又大,動作很困難。當卵子準備好收割時,我走路都疼得忍不住流淚。
醫生取出了 17 顆卵子,其中只有 13 顆夠成熟可以冷凍。常理認為我應該再做一次循環,但這聽起來太痛苦,且財務上有風險。我決定滿足於自己身體所產出的結果。這並不超過平均值,僅僅是平均值。而這一次,這就足夠了。
突然間,我發現自己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我發展了新的愛好:攀岩、背包旅行、學習新舞蹈風格。我不再焦急地滑著交友應用程式,而是閱讀小說。我進行了漫長、隨性的公路旅行。我允許自己和那些不算是認真對象但尊重且有趣的男性發生短暫的激情。我花更多時間陪伴姪女和其他家人。有時候,我什麼也不做。能夠放鬆、玩樂、自我放縱,這種感覺很叛逆。
這和我的女性前輩們的經歷有著巨大的不同。我的祖母在 Instagram 上看到我離經叛道的生活時,打電話來分享她的秘密喜悅。「盡可能地延長妳的青春吧。」她用西班牙語說,「我正在妳身上過著我的夢。」
我從成為家族最糟的噩夢走到了他們從未想過自己能擁有的夢想。我違抗了家族命運的安排。但這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意味著對那些最需要這些幫助的女性來說,這些選擇仍遙不可及。
休息不應該是特權者的專利。拉丁裔女性和所有女性都應該擁有身體主權,包括不僅拒絕生育的權利,還有推遲生育的權利。
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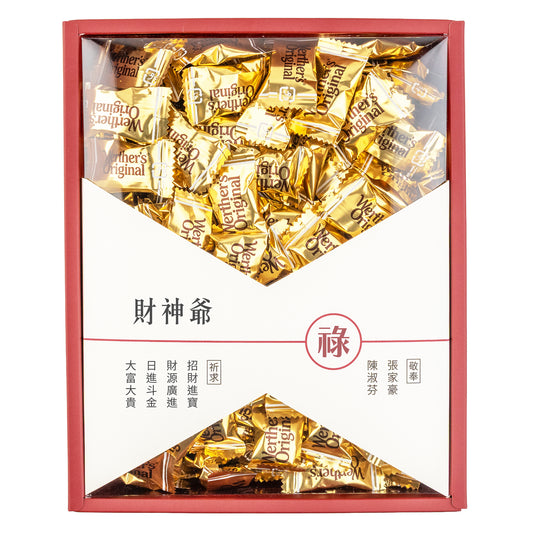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