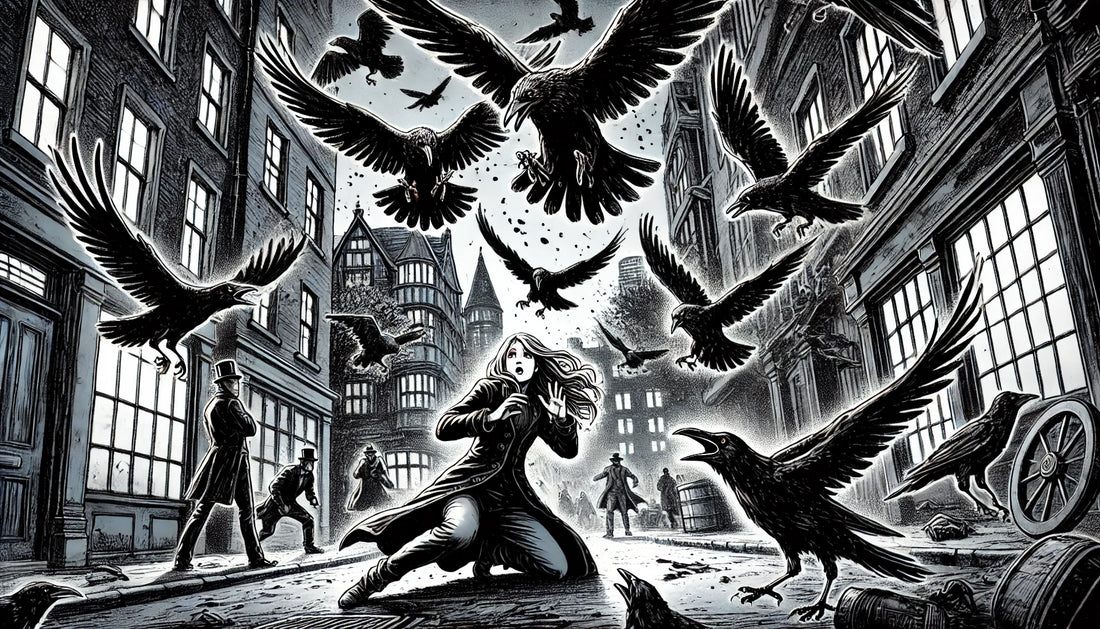
烏鴉長期記憶與多代仇恨:攻擊持續數十年
Share
聰明的鳥兒們懷抱著巨大的怨恨,科學家這麼說。而有些人成為它們憤怒的對象,甚至可能是誤認的受害者。
莉莎·喬伊斯跑著尖叫穿過溫哥華的一條街,而烏鴉一次又一次地攻擊她。
它們俯衝下來,降落在她的頭上,又立即飛走。據喬伊斯女士的計算,這樣重複了八次。那是七月的一個晚上,數百人聚集在戶外觀看煙火,喬伊斯女士想知道為什麼她會成為目標。
「我並不是一個膽小鬼,我通常不會害怕野生動物,」喬伊斯女士說。這個夏天她與烏鴉的遭遇變得如此頻繁,以至於她改變了上下班的路線,以避開這些鳥兒。
「但那真的太無情了,」她說,「而且相當恐怖。」
越來越多人感受烏鴉的憤怒
喬伊斯女士對烏鴉的恐懼並非孤例。CrowTrax,是由溫哥華居民吉姆·奧利利(Jim O'Leary)八年前創建的一個網站,自創建以來,已收到超過8000份報告,記錄了這個樹木茂盛的城市中,烏鴉攻擊人的案例。這些遭遇遠遠超過了太平洋西北地區。
洛杉磯居民尼爾·戴夫(Neil Dave)描述了烏鴉攻擊他的房子,猛烈敲打他的玻璃門,讓他擔心玻璃會破裂。緬因州布倫瑞克的藝術家吉姆·魯(Jim Ru)說,烏鴉摧毀了他住的老人公寓停車場裡數十輛車的雨刷片,無論他們做什麼都無法阻止。
烏鴉因其聰明才智而聞名,它們可以模仿人類語言,使用工具,並在它們的群體(被稱為「烏鴉群」)中的一員死去或被殺時聚集,像是在舉行葬禮。它們可以在人群中辨認和記住面孔。
它們也相當擅長記仇。當烏鴉群將某人視為危險時,它們的憤怒可能相當令人驚恐,並且可以延續超過一隻烏鴉十多年壽命的時間,形成多代的怨恨。
憤怒的烏鴉的攻擊有時彷彿恐怖電影情節,讓人們的生活似乎變成了希區考克電影《鳥》的噩夢。
烏鴉的復仇
西雅圖的電腦專家吉恩·卡特(Gene Carter)被烏鴉跟蹤了一年多,牠們一直守在他家的窗外。
「烏鴉會在廚房窗外盯著我看,」他在一次採訪中說。「如果我在家裡走動,它們會找到任何能棲息的地方對我尖叫。如果我走向我的車,它們會俯衝向我,差點撞到我的頭。」
卡特先生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引發了這些攻擊。有一天他在後院看到烏鴉在接近一個知更鳥的巢,他用耙子向空中扔去。
但他從沒想過烏鴉的報復會持續這麼久。烏鴉群學會認出他乘坐的巴士,並每天在他下班後等待他。「它們每天都在車站等我,」他說,「我的家距離巴士站有三四個街區,它們會一路俯衝攻擊我回家。」
直到卡特先生搬家後,這些騷擾才結束。
專家解析烏鴉攻擊的時機
專家表示,大多數烏鴉的攻擊發生在春季和初夏,當它們作為保護者守護自己的幼鳥,並防止可能的威脅靠近巢穴時。但在其他情況下,攻擊的原因並不那麼明顯。
當烏鴉在七月對喬伊斯女士進行追蹤時,她在當地一個Facebook群組中注意到,她所在的社區裡還有幾個女性也遭到烏鴉的俯衝攻擊,而她們都有長長的金髮。
「我在想這之間是否有某種關聯,」喬伊斯女士說,「它們是不是對金髮的人有仇?」
奧格爾面具與副總統的故事
上個月一個陰沉的周日早晨,一個戴著怪物面具的人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校園裡行走。他經過了幾個潛在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這些人停下校園導覽的腳步,注視著這個看起來像低成本萬聖節恐怖電影演員的人在校園裡走動。
這個戴著面具的人是約翰·馬爾斯洛夫(John Marzluff),一位致力於研究人類與烏鴉互動的教授。馬爾斯洛夫博士對烏鴉的智力有很高的評價。他把烏鴉描述為「飛行的猴子」,因為它們不僅有著卓越的智力,還有著相對於體型較大的大腦。
烏鴉能記仇多久?馬爾斯洛夫博士認為他現在已經解答了這個問題:大約17年。
這個估計基於他2006年在華盛頓大學校園內開始的一項實驗。馬爾斯洛夫博士當時戴著怪物面具,用網子捕捉了七隻烏鴉。很快這些鳥就被釋放了,但馬爾斯洛夫博士說,這次捕捉事件對被捕捉的烏鴉及目睹這一過程的其他烏鴉群成員來說是一場創傷。
為了測試校園內的烏鴉會記住這件事多久,馬爾斯洛夫博士或他的研究助手們會不時戴上怪物面具在校園內行走,記錄有多少烏鴉發出攻擊性的鳴叫聲,專家稱這些聲音為「責罵」。這項實驗進行到第七年時,責罵的烏鴉數量達到頂峰,他遇到的大約有一半的烏鴉都在大聲鳴叫。
根據馬爾斯洛夫博士尚未發表的數據,接下來的十年裡,懷恨在心的烏鴉數量逐漸減少。
在九月的那次走訪中,馬爾斯洛夫博士記錄下他遇到了16隻烏鴉。而自實驗開始以來第一次,它們全部無視了他。
維也納大學專門研究動物行為的認知科學家克里斯蒂安·布魯姆(Christian Blum)博士,受馬爾斯洛夫博士的工作啟發,對烏鴉的近親渡鴉進行了一項類似的多年度實驗。
「它們也是極為擅長記仇的,」布魯姆博士如此描述渡鴉。
在這項從2011年至2015年進行的研究中,布魯姆博士和他的同事們戴上一個面具,拿著一隻死去的渡鴉經過一個充滿活渡鴉的鳥舍。然後他們戴上另一個不同的面具——這是一個對照組,並且在不帶死渡鴉的情況下走過。
就像馬爾斯洛夫博士的實驗一樣,即使沒有死去的渡鴉存在,渡鴉們對於「危險」面具的責罵頻率遠高於對照組。而這種責罵在整個實驗期間持續著,顯示渡鴉的記仇能力同樣非常持久。
「如果你真的讓它們感到厭煩,它們會記恨很久很久,」布魯姆博士說。
馬爾斯洛夫博士在華盛頓大學校園內的實驗也有一個對照面具,烏鴉與其互動的方式——對錯誤的面具進行責罵,可能會給金髮的喬伊斯女士以及溫哥華其他金髮女性的遭遇提供一些線索。
馬爾斯洛夫博士的對照面具是美國前副總統迪克·切尼的面具。雖然被責罵的次數遠少於怪物面具,但仍有少量烏鴉會對它發出鳴叫,他將其解釋為可能存在誤認的傾向。
金髮與烏鴉攻擊
這一點與金髮的西雅圖科學作家琳恩·皮普爾斯(Lynne Peeples)產生了共鳴。大約十年前,她在自家附近的湖邊跑步時,一隻烏鴉對她俯衝攻擊。她感覺到頭頂上一記尖銳的啄擊。
當她繼續跑步時,她看到一個留著長長金色馬尾的男子在追逐並踢湖邊的鴨子和其他鳥類。那個男子看起來精神狀況不佳,皮普爾斯女士懷疑,攻擊她的烏鴉是否把她誤認為那個男子。
不論是否是誤認,烏鴉的攻擊依然持續。同一天她在湖邊被啄後,皮普爾斯女士在她公寓的庭院外用餐,烏鴉輪流向她俯衝攻擊,差點撞上她的頭,最終迫使她轉入室內。
隨後也發生了類似的攻擊。「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每當我看到烏鴉,我都害怕自己會被攻擊,」皮普爾斯女士說。
與烏鴉共存
面對被烏鴉長期追蹤的可怕前景,遭受攻擊的人們在應對上也掙扎著尋找正確的方法。
回到溫哥華,烏鴉受害者能做的很少。市政府的環境專員安琪拉·克蘭普頓(Angela Crampton)表示,該市以擁有繁茂的鳥類群體而感到自豪,包括烏鴉,部分原因是它反映了城市的生態。
「這裡有一個欣賞烏鴉的亞文化,」她說。
克蘭普頓女士表示,市政府的主要信息是「共存」,並且當局不會移除烏鴉的巢或修剪樹木來減少攻擊。
這種「接受現狀」的信息對魯本·希門尼斯(Ruben Jimenez)來說相當令人沮喪。去年春天,他搬進了擁有大陽台的新公寓。希門尼斯先生種植了羅勒、薰衣草和歐洲七葉樹,但每次他走到陽台去照顧植物時,幾乎都會被攻擊。
「它們會俯衝下來攻擊我,」希門尼斯先生說。「這很嚴重,我甚至睡不著,因為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他的妻子喜歡取笑他——一個身高6英尺3寸、重230磅的大男人,居然害怕幾隻鳥。(烏鴉並沒有騷擾他的妻子,不知何故。)
希門尼斯先生掛上了閃亮的金屬絲,在窗戶上貼了反光膠帶,甚至在陽台上放置了一隻假貓頭鷹,頭在風中搖晃。但這些都沒有效果。
他回想起自己在多米尼加共和國長大時,當地人是如何對付烏鴉的。他家附近教堂的一位男子時不時會帶著氣槍在教堂四處走動,驅趕停在建築物上的鳥類。
「我被攻擊時給我爸打電話,解釋我不能在加拿大射殺烏鴉,」希門尼斯先生說。「他在電話裡笑著說,『如果烏鴉飛到你家裡,你是不是得搬出去住?』」
用食物來賄賂烏鴉
在溫哥華,其他一些被烏鴉騷擾的人,最終與這些鳥達成了一種妥協。這往往以他們稱為「賄賂」的方式來實現。
十年前,溫哥華電台主持人吉爾·班尼特(Jill Bennett)在遛狗時遭到烏鴉無情的攻擊,她只能躲進一個停車場。
「我從來沒有對烏鴉做過任何不友善或暴力的事情,」班尼特女士說。
當再次遭到攻擊時,班尼特女士開始隨身攜帶狗糧和花生,在散步時分發這些零食。
一對烏鴉開始跟隨她,成為她的「保護者」。
當今年夏天,一隻有著獨特羽毛的第三隻烏鴉對她俯衝攻擊時,這對烏鴉保護者反擊了,將這隻入侵的烏鴉趕走了。
班尼特女士將她餵烏鴉的行為比作黑幫式的勒索。她說這就是「保護費」,是為了知道自己不會受到空中攻擊而支付的代價。
「我把它稱為烏鴉稅,」她說。
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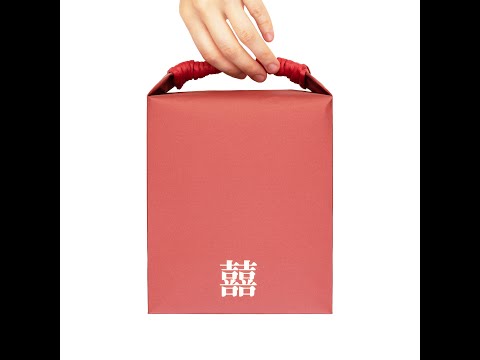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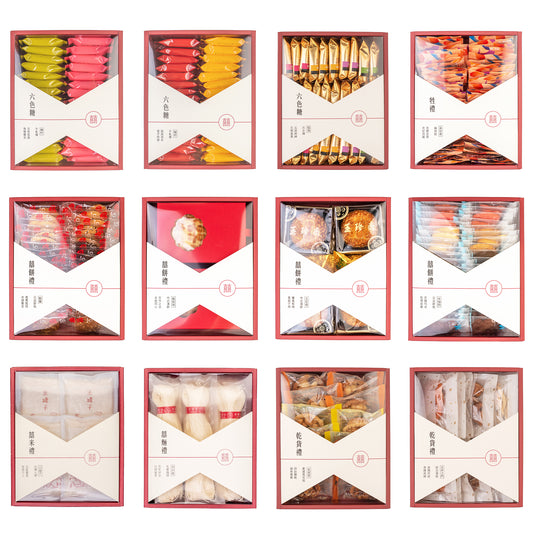
![訂婚文定儀式.六禮十二禮自由配 [經典紅]](http://wish.with.tw/cdn/shop/files/preview_images/hqdefault_360f1d3b-fff8-48dd-9c89-c854ffdb803d.jpg?v=1690222239&width=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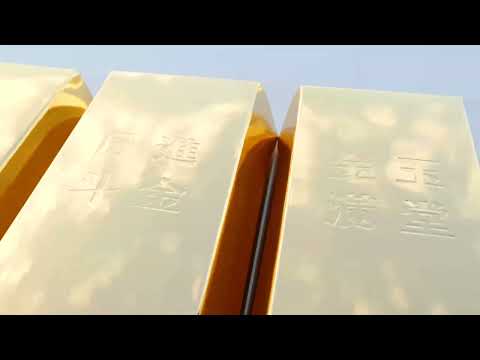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