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脫衣舞孃的心聲:男友無法看見我的真實
Share
作者是脫衣舞孃,而她的男友卻透過顧客的眼光看待她
我的工作意味著獨立、療癒和自由。為什麼我的伴侶看不到這一點呢?
我24歲開始脫衣舞的工作。當時我和一位朋友在沙發上喝茶,我們是兩個在柏林的年輕理想主義者,討論著我們需要賺錢。從那時起,一切發展得出乎意料的快速,就像這個行業常常發生的一樣。我的朋友在Craigslist上看到了一個廣告,不久之後,我們就發現自己穿著半裸的服裝,在煙霧瀰漫的脫衣舞俱樂部走廊裡踉蹌前行,腳上踩著高跟平台鞋。
如今,我已經有六年的工作經驗,對這個行業的看法也比當初在茶時間的交談中更為細膩。然而,這些年來有一個問題始終不變,那就是人們經常問我這個問題:“妳有男朋友嗎?他對妳的工作有什麼看法?”
不論這個問題以什麼樣的變體被提出(“有這個工作妳能找到男朋友嗎?”“妳男朋友不會嫉妒嗎?”),它總是預設我有一個男朋友。至於我可能被女性吸引的可能性,則很少有人提及。
在我的經驗中,脫衣舞俱樂部仍然受到傳統性別規範的束縛。非典型性別表現在這裡並不受歡迎,而令人震驚的恐跨性別情緒則浸透了俱樂部臭烘烘的、沾滿香檳的地毯。女性形象的脫衣舞孃被期望表現出超級女性氣質,而男性顧客則通過表現出過度的陽剛氣質和財力,無論是真實的還是偽裝的,來展示自己的男子氣概。
在這樣的環境中,異性戀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隨著歲月的推移,我逐漸意識到,脫衣舞俱樂部並不是一個平行宇宙;它更像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只是被明亮的燈光放大了而已。這也反映在我作為一個脫衣舞孃與異性戀男人的第一次戀愛關係中。
當我第一次遇見後來成為我男友的那個男人時,我告訴他我的工作和我的雙性戀身份,他聲稱對兩者都很淡然。他自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還告訴我“跟一個脫衣舞孃約會很酷”。然而,當我們的關係正式化後,問題就開始出現了,他開始對我的職業選擇表達不滿。我見過很多同事的伴侶都出現過這種情況,但與他們不同的是,我的男人自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為什麼你不喜歡我的工作?”我問他。我送給他一本《權力的遊戲》食譜,我們度過了一個充滿樂趣的日子,煮了幾道我們再也不會煮的奇怪菜餚。我忍了大約六個月,直到這個問題終於爆發出來。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說。“我就是不喜歡,可能永遠不會喜歡。”
我放下叉子,食物突然變得索然無味。
儘管如此,我還是和他在一起。我知道,戀愛關係是由妥協組成的。
我留下來,並試圖讓這段關係奏效。我認為,如果我向他展示我的世界,他會意識到他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當我把他介紹給我的脫衣舞孃朋友時,他低著頭坐在桌旁,一句話也不說。
我開始策劃旨在去污名化脫衣舞並探索其創意面的活動。我邀請他參加每一場活動,但他從來沒有出現過。每次我去工作時,他都在家裡抱著頭痛。
在這段關係進行了一年後,他仍然會說出類似“我的朋友們問我怎麼能跟一個脫衣舞孃在一起”這樣的話。
他本有機會從我的經歷中學習和理解。相反,他只是重複他那些從未和脫衣舞孃交談過的朋友的判斷。
我決定採取震撼療法。
在一個工作日的平靜夜晚,我遇到了一個有趣且有錢的顧客,他待到了俱樂部關門。當酒吧招待宣布最後一輪時,這個人提議給我錢,讓我在他的酒店繼續派對,這只是一個社交活動,並非性活動,而且我採取了約會時會採取的所有預防措施,比如向朋友發送我的位置和每小時更新情況。酒店原來是麗思卡爾頓。
作為一個在意大利北部工人階級家庭長大的鄉村女孩,我對豪華場所並不習慣。脫衣舞有一種了不起的能力,可以彌合階級之間的鴻溝;它讓我接觸到了豪華酒店、香檳和昂貴約會的世界。
然而,我內心的工人階級女孩從未消失,當我看到套房裡的大理石浴室時,我覺得在麗思卡爾頓的浴室裡拍一張幾乎裸體的屁股照會很有趣。我脫下運動褲,只剩下內衣,擺好姿勢。顧客拍了照片,我把它發給了我男友。當時是早上7點,你可以看到照片裡顧客的膝蓋。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我發這張照片是有邏輯的。我是想向他表明我沒做錯什麼,因為如果我真的做了錯事,怎麼會發照片給他呢?
但顯然這種邏輯並不那麼成立,因為所有的朋友都說我的想法毫無道理。事實是,我想激怒他,想要表達某種立場。他對我的脫衣舞工作如此敏感,又如此批判,以至於我希望通過轟炸他這類內容,最終讓他對我的世界感到習以為常。
發送照片後,我三天都沒有收到他的回應。這讓我意識到:我的男朋友透過顧客的眼光看我,像那種不了解脫衣舞是表演過度性感和女性化,且作為專業娛樂的人。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一位空姐在問你是否要橙汁時微笑,你會覺得她真的喜歡你嗎?還是認為她是在履行工作職責?對於脫衣舞孃也是一樣。我們脫掉衣服,表現出誘惑性,不是因為我們愛上了顧客,而是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如果我的男朋友曾經去過脫衣舞俱樂部,他可能會成為那種顧客,會問你要電話號碼或者在你下班後想請你去吃早餐,因為他們將交易性的聯繫誤以為是真實的關係。
最終,我們分手了。矛盾的是,他本應對我們的關係感到安心,因為我在脫衣舞俱樂部工作,隨著工作的時間越久,我在業餘時間對男人的吸引力就越低。事實上,他應該擔心的是我可能會愛上我的脫衣舞同事,但與他對待男性顧客的態度相反,他從未將她們視為威脅。
正如他將我作為脫衣舞孃的身份物化,他也將我的雙性戀身份物化,這是許多異性戀男人常有的行為。人們常常認為雙性戀是對與任一性別的人發生性關係持開放態度。這種看法總是讓我感到被否定,讓我很不舒服。
我並不是“開放”於與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想法”。我會愛上女人,我渴望她們。我的男朋友應該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花了無數小時聽我講述過去那些同性戀情感破裂的故事,聽我如何因為同事給我發出混亂信號而把我放在朋友區後痛哭流涕。
然而,他的嫉妒從未針對過女性,他從不將她們視為競爭對手,這意味著他從未真正認真對待我的酷兒身份。他的物化表現得很明顯,他喜歡當我評論某位同事很性感,並將他的口味與我的口味進行比較。
他可能從未想過為什麼他不喜歡我的工作,就像他所說的那樣——但我想過。而我認為,他把我的身體視為他的財產。他無法忍受陌生人看到我裸露的身體,揭示了他認為應該只屬於我們臥室隱私的秘密。他早期的話語透露了他的真實想法:“跟一個脫衣舞孃約會很酷。”彷彿我是他架子上的一個獎杯,一個穿著蕾絲內衣的性感雕像。
他沒有看到脫衣舞如何給了我經濟獨立,讓我得以環遊世界。他沒有看到這份工作如何治癒了我那嚴苛宗教背景下的創傷,讓我擺脫了大量的天主教羞恥感。他沒有看到這份工作如何讓曾經不自信的孩子變成了他喜歡的那個自信的人。
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那展示給陌生人的裸露胸部。對他來說,脫衣舞僅僅被簡化為將我的肉體公開的罪行——因為在他看來,其他男人比其他女人更重要。最終,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看見了真正的我,那個內心驕傲、全心全意去愛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樣,我也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
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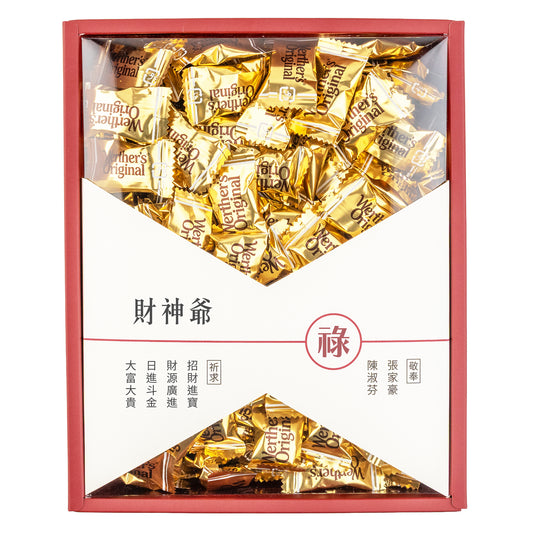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