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抗憂鬱藥激增,SSRI恐改變一生性生活風險真相解析
Share
成人服用S.S.R.I.的研究顯示,這類藥物會壓抑性慾。為何我們不研究,這對服藥的青少年可能意味著什麼?
Marie在15歲時開始服用fluoxetine,也就是Prozac的學名藥。這種藥是一種S.S.R.I.(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是她在一個針對飲食疾患的日間治療計畫中,療程的一部分。這種藥對她的性產生了代價。「我很早就能連結到最初的性衝動火花,」她說,記得自己早在6、7歲時就有迷戀的對象。就在開始用藥前不久,她還曾遠遠地被學校裡一個藍眼睛的冰球選手迷得暈頭轉向,他高大、有趣又有魅力。她回想起那個男孩在她心中激起的慌亂與幻想。但在用藥之後,她感覺那股迷戀很快就消失了。
「接著,」Marie說,「我意識到,喔,我沒有再發展新的迷戀對象了。」她完全不知道藥物可能是原因:「沒有人告訴我有性方面的副作用。」
即便飲食疾患最嚴重的階段逐漸緩解,精神科醫師和家庭科醫師仍告訴Marie和她的父母,她應該持續服用抗憂鬱藥。她順從地照做,同時一次次嘗試卻始終無法逃離性副作用。她把fluoxetine換成其他抗憂鬱藥,包括另種類型的抗憂鬱藥Wellbutrin,而這種藥有時被開來對付性慾低落。她現在38歲,已經停用精神科藥物六年。但性慾仍然缺席。「對我來說,那裡就像一個空無一物的黑暗空間,」她說。「什麼都沒有。」
Marie告訴我,她有PSSD,也就是post-S.S.R.I. sexual dysfunction,意指停用S.S.R.I.之後仍持續存在的性功能喪失。這是一個備受爭議的稱呼,因為雖然S.S.R.I.的性副作用早已廣為人知——慾望減弱或消失、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女性難以興奮、高潮延遲與鈍化,或完全無法達到高潮——一般仍普遍假設,這些副作用會在藥物離開體內後完全消失。一些精神科醫師懷疑,PSSD其實不是藥物後遺症,而是由最初讓病人被開藥的問題所造成。憂鬱本身就會扼殺性;焦慮也是,這是患者被處方S.S.R.I.的另一主要原因。
然而,專業界對PSSD的認可正悄悄發生轉變。最新版本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指出,「在某些案例中,serotonin-reuptake-inhibitor-induced sexual dysfunction(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誘發的性功能障礙)可能在停藥後依然持續。」歐盟的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也發布了類似的警示,加拿大、澳洲與香港的藥政機關亦然。在美國,Prozac已附上相關警語。消費者倡議團體則正在敦促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要求所有S.S.R.I.——這也是最常被處方的抗憂鬱藥物類別——都必須標示此類警告。臨床醫師已在學術文獻中發表超過500篇關於PSSD經驗的病例報告。《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在2020年的一篇社論中主張:「Post-S.S.R.I. sexual dysfunction是被低估的問題,且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可能極具削弱性。」
PSSD的統計風險仍不清楚。近來為數不多的相關研究,充滿各種限制。估計發生率從「非常罕見」到「相當常見」都有。在一項研究中,勃起功能障礙影響不到1%的前S.S.R.I.使用者;但另一項研究則發現,至少13%受訪者出現生殖器麻木。然而不論哪個數字,PSSD對年輕人而言可能都具有迫切意義。
為了撰寫本文,我訪問了20多位有PSSD的人——大多在美國,也有少數在加拿大、英國與印度。(他們目前年齡介於23到45歲之間,並要求只使用名字或中間名,以保護隱私。)雖然這個狀況也會出現在成年後才開始服用S.S.R.I.的人身上,我主要聚焦在那些在青少年甚至更早就開始用藥的人。我感興趣的不只是他們極端的經驗,也包括他們的案例如何反映較典型的經驗。
如果副作用是沿著一個強度與持續時間的光譜發生——從幾乎可忽略到難以承受,從短暫到在停藥後無限延長——那麼那些受影響最深的人所描述的情況,就成了光譜中段可能正在發生什麼的徵兆。在那裡,在較常見的反應範圍內,S.S.R.I.的副作用很可能正在干擾年輕人性慾的發展。它們可能在性慾自然飆升的時期強加一段休眠期——比Marie那樣的情況隱晦些,卻仍然造成重大的干擾,而且也許帶來持久的後果。完全發展成PSSD的案例或許罕見,但它似乎暗示,抑制新萌芽的性可能帶來更常見且重要的影響。
隨著S.S.R.I.處方量激增,這些藥物對年輕人性發展的影響顯得格外重要。在美國,大約有兩百萬名12到17歲的青少年正在服用S.S.R.I.。《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期刊在2024年刊登的一項大型研究,逐月統計2016至2022年間,這個年齡層填領抗憂鬱藥處方的比例。在此期間,比例上升了69%,新冠疫情帶來的情緒餘波幾乎可以確定是一個因素,儘管在那之前就已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根據一項在2023至2024年間進行、超過10萬人參與的調查,在大學生當中,22%的人在前一年內曾服用抗憂鬱藥。這個數字在2007年時只有8%。
對許多人來說,這些藥物能讓他們從沉重的憂鬱或侵襲式的焦慮中獲得解脫;對某些人而言,藥物甚至能救命。這些藥可能避免自傷或自殺。但一些臨床醫師認為,很有可能的是,S.S.R.I.同時也在性方面帶來某種破壞。
19歲那年,因為搬離家庭、開始上大學的壓力,Cael被處方了一連串S.S.R.I.與S.N.R.I.(selective 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選擇性血清素與正腎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劑,與前者類似的一類藥)。(在許多美國以外的國家,S.N.R.I.同樣必須標示PSSD警語。)他說,性功能障礙與這些藥如影隨形:勃起不穩定,而且就算勉強能達到高潮,那種高潮也彷彿是沒有快感的抽象概念。Cael現在23歲,停藥一年半。失去的東西始終沒有回來。他不禁反覆思索這會不會是永久性的。「如果我這輩子都要這樣怎麼辦?」他問。
我聽過最讓人揪心的PSSD故事之一,來自一位母親。Ruth告訴我,大約在二十年前,她的女兒在11歲時被精神科醫師處方Zoloft(一種S.S.R.I.),起因是學校發生了一件羞辱她的事件,「讓她感到有點不對勁、很焦慮。」對那次開藥,Ruth說:「我大概覺得那是好事吧。」她談到自己當時的天真,以及對精神醫學的「盲目信任」。她的女兒最後在這種藥物上待了整整十年,一直到2011年。直到近幾年,Ruth才從女兒口中得知,那些她至今仍承受的性副作用,以及她的哀傷。「她的敏感帶不再有反應,」Ruth說。「這讓我深感悲傷,因為我們的性,我們從身體與與他人親密中得到的愉悅,是那麼美好的經驗;它讓我們感覺自己不是孤單一人。」回想起來,Ruth說:「我有巨大的、可怕的悔恨」,為自己當年允許孩子用藥。「我不敢相信當時竟然那麼輕易就說好。」
大約二十年前,Alexander Scharko醫師就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上敲響警鐘,提醒S.S.R.I.可能對年輕人的性成熟帶來影響。當時身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博士後研究員,他試圖分析既有研究,看S.S.R.I.是否會在青少年身上造成性功能障礙。但他發現,根本沒有相關研究,只有幾則病例報告的零星數據。
在那篇論文中,Scharko先描述了成人使用S.S.R.I.時,眾所周知的性副作用問題。接著他主張,青少年身上很可能也是如此。他提出,藥物可能正在扭曲年輕人的情色發展。他問道:「在兒童或青春期使用S.S.R.I.,會不會對成年後的性功能造成負面影響?」他強調,目前缺乏正式的研究。
可信賴的數據,需要那種精心設計的長期研究,而這類研究在精神科藥物上極少被執行,部分原因在於藥廠資助了大部分精神科藥物研究,而公司對於弄清病人長期狀況好壞,並沒有太大的財務誘因。Scharko也想知道,這種忽略是否也延伸到臨床醫師與個別病人的互動之中:「臨床醫師或許在給青少年開S.S.R.I.時,沒有詢問他們關於性與性功能的問題。」
Scharko原本預期他的論文會引起不小的騷動。但當我最近與他談話時,他說起論文發表後幾乎完全的靜默,而且這種靜默至今仍在持續。「自從我在2004年發表那篇文章之後,」他說,「我幾乎沒再看到什麼關於這個主題的東西。」他身為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醫師的職涯,橫跨約翰霍普金斯與賓州大學等醫學院的教職,到大型醫院中專門照顧有嚴重身心共病兒童的臨床工作。他的專長之一是兒童精神藥理學。他經常為病人開S.S.R.I.,但他對這種藥物廣受擁抱、使用量快速上升感到憂心。「雖然在青少年族群中已經有臨床試驗,」他說,而那些試驗的確有檢視口乾、噁心等副作用,「但我沒看到他們在評估不良反應時,詢問任何性方面的問題。我也沒聽到同儕在談這件事。」
如今情況仍和2004年時差不多:沒有專門針對年輕人的性副作用研究。我們所擁有的,只有從成人研究推論而來的資料。根據2019年刊載於《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的一篇研究,視症狀種類、藥物與使用時間長短而定,大約有30%到80%的成人服用S.S.R.I.後,在不同程度上出現性慾減退、感覺鈍化與功能受損。(因為能預期地鈍化性反應,S.S.R.I.長期以來也被「超適應症」用來治療早洩。)因此,雖然尚未證實,我們仍可以推測,服用這類藥物的年輕人中,也有類似比例的人會經歷自身性一面的暗淡。
Scharko談到一種奇特的失調:一方面,整體文化充斥著性;另一方面,在談論「青少年與性發展」時,卻存在著不舒服,甚至某種「禁忌」,他這麼說。這種不自在,不只是影響臨床醫師,也「當然會影響父母」,而且「當然也會影響青少年自己」。結果便是普遍的迴避。
「這些藥非常有力,」他說,「而我們不知道,它在兒童與青少年身上可能帶來多廣泛的不良影響。」他談到年輕大腦的特別可塑性與「脆弱性」,並抨擊這方面研究的持續真空。性自我形成的關鍵時期,在他看來幾乎被刻意忽視。「如果我替一個學齡兒童」為了強迫症開立S.S.R.I.,「而這個孩子對藥物反應良好,於是持續服用,接著進入青春期,那會發生什麼事?我沒辦法真正告訴你。」他補充說:「但我猜,多多少少一定會有什麼事發生。」
Amir Levine醫師是另一位呼應Scharko憂慮的精神科醫師。2015年,他在《Pediatrics》期刊發表論文回應Scharko的文章,重申他那「大致上被忽視」的訊息:用Levine的話說,就是「我們對整個族群都沒有問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也就沒有正面面對、也無從理解S.S.R.I.對性成熟的影響。「這是臨床研究中非常令人遺憾的遺漏,」他說。
他指出,這些藥有時會帶來「近乎奇蹟」的效果。雖然他現在的門診多半是成人,他仍記得有一位年輕病人,原本因為焦慮嚴重到無法上學,但在服藥幾個月後,竟然能快樂地去參加夏令營。接著,他又回到了藥物可能影響新萌芽的性這個問題——「你給病人一顆藥,它有可能長長久久地改變他的性生活。」
對某些人而言,S.S.R.I.的性副作用可能與特定的生理反應有關。Irwin Goldstein醫師剛完成一項對陰莖內部組織的影像研究,研究中利用注射誘發勃起,再以超高解析度的超音波技術進行成像。Goldstein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泌尿學臨床教授,也是性醫學專家,每年接診50到75位勃起功能障礙新病人。在他的研究中,有38名受試者因勃起功能障礙而前來看診,並將自己的陽痿追溯到過去使用S.S.R.I.。這一組年齡介於16到43歲之間,停藥中位數為21個月。研究設有兩個對照組:一組的勃起功能障礙來自外傷,例如越野機車事故、長期自行車座壓迫,或被人踢到跨下;另一組則是年過50、且被診斷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與高膽固醇等已知會增加勃起困難風險的男性。兩個對照組皆無S.S.R.I.使用史。
Goldstein向我展示每一組受試者的超音波綜合影像。在第一組中,陰莖內部組織呈現一片黑色,代表膠原蛋白過度聚集。這是瀰漫性的疤痕化,足以強烈導致勃起功能障礙。Goldstein進一步說明,在陰莖中,S.S.R.I.可能促使過量氧自由基的產生,導致疤痕化與功能失調。在超過50歲那組的陰莖組織中,也可以看到同樣鮮明的退化。S.S.R.I.在陰莖組織上的生理影響,與老化及既知會造成勃起功能障礙的疾病影響十分相似。他說,這提供了一種很明顯的生理機制,說明PSSD如何形成。至於那組因跨部外傷導致勃起困難的人,則沒有出現此類退化。
其他導致PSSD的機制,或許更難辨識,可能潛藏在心理深處,以及心理與腦部生化之間曖昧難解的關係中。由於大腦極度繁複,某種程度的盲區,或許註定會存在於精神科藥物的科學與實務使用中。在腦內,S.S.R.I.會增加血清素(serotonin)這種神經傳導物質的可用性,而這可能促進幸福感、阻擋沮喪、壓低自我貶抑的聲音、平撫恐慌,並在整體上幫助人們應對生活。但這些藥物對其他神經傳導物質、對荷爾蒙、對細胞基本電性特質,以及對無數神經交互作用的影響,目前的了解多半仍停留在推測的層次。
考量到S.S.R.I.在腦中可能造成的難以估量影響,以及在我們的心理世界裡,性與自我認同以難以定義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就不難理解為何PSSD患者會說自己在性之外也遭受持久的損害。情緒的鈍化往往伴隨PSSD而來。Cael談到自己對父母、兄弟姊妹的感受時說:「我再也覺得跟他們沒有連結了。我可以好幾年不見他們,也不會想念。」
另一位年輕男子Sean,說的是另一種PSSD故事。三年前,他在22歲時被處方Celexa(一種常見的S.S.R.I.),因為他長期承受的焦慮在大學期末考期間變得難以忍受。他描述的反應快到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雖然對PSSD患者而言,這樣的速度並非聞所未聞。他服用的是中等劑量:一顆10毫克的藥丸。約一小時後,他說:「我的生殖器就麻掉了。」他幾乎立刻停藥,此後再也沒有服用任何精神科藥物。「三年過去了,」他解釋,他的陰莖「摸起來就像我的手肘——如果你碰我的手肘,就是那種感覺。」與生理的麻木相伴而來的,是情感的麻木。「我沒辦法對任何人產生連結——我覺得我的靈魂像被從身體裡扯出來。」他這麼對一小群最親近的朋友說。他試著讓醫師認真看待他的狀況。「他們說:那是不可能的。這一切都只是你想出來的。」
另一種交纏的痛苦,是創造力的消失。Marie記得自己在高中開始服用fluoxetine後,失去了即興創作的能力。突然間,她說:「我再也無法進入那種flow state(心流狀態),」無論在鋼琴上或其他樂器——長笛與薩克斯風——都是如此。當她去幫忙帶小孩,而孩子們要她像以前那樣投入假裝遊戲時,她幾乎無法跟著一起玩。「我試著伸手去抓,」她說,「但那東西已經不在了。」對Marie來說,創造力與幻想,在情色與非情色的面向上,都仍然被封閉著。「有時我覺得自己像個機器人。」
Tami Benton醫師是費城兒童醫院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與行為科部門的主任。我先與她談論S.S.R.I.與性,接著又訪問了她同部門的同事Penelope Carter醫師。回想起自己與考慮服用或已經服用S.S.R.I.的青少年病人進行初診與回診的情況時,有著三十年資歷的Benton說:「我一定會提到性方面的副作用,不論你現在是否有性行為。年輕人經常會有自慰等性行為,而我們知道S.S.R.I.會影響高潮能力、會影響你的性能力與性經驗——我們必須問青少年這些事。」
當我問Carter如何與青少年談知情同意時,她回答:「那確實是一個可能的副作用。如果你去Google,一定會看到。所以我會提到,因為他們一定會看到,我不希望他們心裡想:為什麼我的醫生沒跟我說?我不信任我的精神科醫師。如果你不信任整個過程,你就不會變好。」
Benton與Carter都談到自己不會急著替病人用藥,並強調心理治療在治療計畫中扮演關鍵角色。Carter指出,憂鬱或焦慮可能造成的麻痺式孤立感,或者自傷風險,常常會讓用藥成為必要。他們所關注的,是這類情緒上的困境。Benton說,在她最近所看的用S.S.R.I.的青少年病人中,性副作用很少被提出。這與成人研究所暗示的情況不太一致。在訪談中的某個時刻,她反省道:「我也在想,我們在詢問性副作用這件事上,到底做得好不好。」
Carter則把這個議題視為次要。「青少年的性慾本來就很高,」她說,男孩們「風吹過來都會勃起」,因此在她看來,相較於放任憂鬱不治,性慾減少沒那麼令人擔心。服用S.S.R.I.之後,「有些男孩與女孩看到心儀對象時,可能不會出現那種va-va-voom的感覺,」但整體而言,藥物「相當溫和無害」。不管如何,她說:「停掉S.S.R.I.,高潮就會回來,性慾也會回來。」
「性副作用是暫時的」這種信念,在開藥醫師之中非常普遍:停藥之後,性就會完全恢復。但Marie、Cael與Ruth等人的故事,以及來自動物實驗的證據,似乎都另有說法。在2010年刊載於《Biological Psychiatry》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在雄鼠青春期給予一種Prozac學名藥,等到藥物有足夠時間從牠們體內排除後,再在牠們成年時、置於有性接受度的母鼠面前,觀察其性行為。與對照組相比,曾經用藥的雄鼠在爬跨行為上慢得多,從開始交配到射精所需時間長得多,而且在單一實驗時段內,射精次數也少得多。並非所有類似實驗都得出如此明確的數據,雌鼠的結果也比較模糊,或許是因為雌性囓齒類的性行為更難測量。不過整體來說,這些囓齒類研究帶有警訊意味。
Liz的故事交織了性喪失與其他深層轉變。而和Marie一樣,Liz的故事也與音樂有關。約16歲時,因為覺得父母不願聽她說,她去找家庭科醫師,訴說自己在學校感到恐懼——她被霸凌,包括被丟石頭、被推倒在地。依她的記憶,在大約15分鐘的問診之後,醫師判斷她需要用藥,在便利貼上畫了一個簡略的大腦神經元示意圖,解釋她的血清素偏低,然後開給她Seroxat,也就是英國版本的Paxil,一種S.S.R.I.。
如今45歲的Liz,在那之前,是一個會一邊自慰、一邊幻想演員Jeff Goldblum的女孩。「我在『The Fly』裡很迷他,」她說。「當然,是他還沒變成蒼蠅之前。」她也是一個承繼了父親與祖母鋼琴天分的女孩。從三、四歲起,她就會坐在一旁,隨著父親彈奏拉格泰姆,靠耳朵在高音區補上旋律。沒多久,她便不斷練習:莫札特、蕭邦,以及那些觸動她的流行歌,並在其上加上裝飾與即興,在一個音符的微小改變如何扭轉整段樂句情緒這件事上著迷。她會把電視靜音,為畫面配上自己的配樂。到了青少年中期,她想像自己將來會在大學主修音樂,然後投入電影配樂的職涯。
Liz說,Seroxat熄滅了她的性衝動;它似乎也偷走了她曾在聆聽、演奏與創作音樂時感受到的那種敏銳而精緻的感受——「像脊椎發麻一樣」的感動。那消失之後,她的藝術決心與創意也一併消散。「那種感覺和性有某種連結。一切都變得機械化、公式化。我無法在鋼琴上發明新東西。」她的志向就此偏離軌道。
這些年來,Liz一再試著把自己從Seroxat身上解脫出來,歷經了無數次反覆。她出現了戒斷症狀——這個問題如今已被廣泛承認——但醫師一次次把那診斷為憂鬱復發,叫她回到藥物懷抱,而她也聽從了他們的判斷。後來,她決定再試一次。非常緩慢地,她現在成功把劑量減到幾乎不存在,目標是完全停藥。好幾年來,她一直維持在遠低於治療劑量的水平。即便如此,她說:「下面仍然完全沒有感覺。」無論感覺或慾望,都沒有復甦跡象。然而,她開始隱約感到音樂帶來的感動,於是又重拾琴鍵。
某個下午,在她塞滿東西、空間不比小型更衣室大的房間裡,她坐在電子琴前,彈奏蕭邦與〈I Only Have Eyes for You〉的片段,技巧之好毋庸置疑。那音樂時而動人,卻又被突然的節奏斷裂或尋找音符、和弦的停頓打斷。她彈著彈著停下來,再重新開始,又停下來。她為自己多年以前的人生偏離而落淚。
任何企圖徹底研究PSSD的努力,都必須面對一個難題:如何區分S.S.R.I.的作用與那些原本為了治療而用藥的憂鬱、焦慮與其他心理困擾本身的影響。如果醫師對像Sean這樣的病人說「這都是你想出來的」其實是對的呢?如果Marie與Liz錯把藥物當成替罪羔羊,而真正根源其實是她們心理上的挫折與失望呢?
在Reddit的r/Psychiatry版——一個精神健康專業人員的論壇上,要找到這樣的觀點並不難,PSSD相關討論時尤其如此。有人發文說:「病人堅稱自己的性與人際困難,完全是因為曾經嘗試過僅僅5毫克的escitalopram。」發文者使用的是Lexapro(一種主要S.S.R.I.)的學名,並轉述這是另一位醫師遇到的案例。「當我同事向病人解釋,這些症狀更可能由深層情感與人格問題解釋時,病人非常憤怒。」
除了未知數之外,還有一段令人不安的歷史:專業圈長期否認S.S.R.I.的性影響。當這類藥物在1980與1990年代初首次上市時,製藥產業與許多開藥醫師的預設立場,是淡化性副作用,稱其為不常見。1995年的《Physicians’ Desk Reference》宣稱,只有1.9%的fluoxetine使用者出現性功能障礙。精神科醫師Peter Kramer在1993年出版的暢銷書《Listening to Prozac》中,多半把性副作用放到註腳,大多只有在書末提及;在正文裡,他也只有一次觸及此事,把它描述為對一位過度沉迷色情的丈夫而言反而是一種好處。
如今,精神醫學界大致已承認成人使用S.S.R.I.時,性副作用發生率很高。我為本文訪問的六位精神科醫師,也都提到在開立處方時,讓青少年病人知道這種可能的重要性。他們也提到,視各州關於同意權的法律而定,有時必須讓父母也了解。但在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擔任臨床副教授、同時看診青少年與成人的Awais Aftab醫師認為,大多數開藥醫師並沒有進行這樣的對話。「我只知道極少數精神科醫師會把這當作潛在副作用說明,」他說,他的判斷來自那些看過其他醫師、後來轉到他門診的病人,來自他對在職住院醫師的教育工作,以及與同儕的談話。他補充說,真正在醫療實務上落實知情同意,其實非常罕見。醫師「也許會叫你看一張說明小冊子,」他說。「這就是現在的文化:這是我為你推薦的藥。」
渥太華大學醫學教授Peggy J. Kleinplatz,則分享了一個畫面,讓人一窺家庭科與其他基層醫師——也就是在美國與加拿大開出多數S.S.R.I.處方的人——在知情同意上的實際做法。2019年,Kleinplatz在一場加拿大家庭醫師醫學會議上發表演講。她問台下大約50位醫師,有多少人知道S.S.R.I.有性副作用。「大約80%的人舉手,」她估計。接著她問,有多少人在開藥時告訴病人這件事。「只有一隻手舉起來。」於是她再問,為什麼不說?「他們說是因為病人用藥順從度的問題。」依據他們的擔憂,如果告知可能出現性副作用,就有風險讓病人拒絕他們認為必要的藥物。
半退休精神科醫師Jim Phelps,在職涯中多半專注於情緒疾患,並長期在綜合醫院與大學健康中心擔任會診,他指出,開藥醫師正面臨「自律與行善」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是讓病人完全了解的自主權,另一方面則是由醫師主導的某種善意獨裁。他解釋說,這個問題在S.S.R.I.上特別棘手,因為這類藥物療效的一部分可能倚賴安慰劑效應。他估算安慰劑效應大約佔35%,並表示,如果你向病人說明性副作用,從而「攪亂」病人對藥物的樂觀期待,就可能失去這一塊安慰劑加成。
Levine則提出另一個開藥醫師可能避免和青少年談性副作用的理由——害怕被貼上不恰當,甚至更嚴重的標籤。「對某些臨床醫師來說,和青少年談性副作用,就像踏進地雷區——但我們必須想出方法,讓這些對話變得可能,即使是透過標準化的症狀檢核表,來幫助啟動對話也好,」他說。
至於性副作用在停用S.S.R.I.後依然持續的風險,我訪問的這些看診青少年的精神科醫師中,沒有一位表示自己會在知情同意流程中提到這點。Aftab解釋說,現階段還沒有足夠的研究能釐清問題的範圍。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教務長教授、國際性研究學會前任會長Debby Herbenick,談到對於S.S.R.I.對年輕人性的影響進行嚴謹研究的必要性時說:「這真的是個很大的議題。」她說,我們「應該在乎年輕人是如何發展,以及他們正在服用的藥物如何可能影響到他們的正常性發展。」
一位名叫True的年輕男子,則提醒我們,有時性副作用的重要性遠不及痛苦本身。他25歲,從16歲起幾乎一直在吃fluoxetine,中途只在大約21歲時停過一年半。他開始吃藥,是為了應付圍繞在高中成績與大學入學考試上的焦慮風暴,那些考試讓他覺得「彷彿要決定我的整個人生,」他說;他也害怕學校會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心理治療沒有幫上多少忙,至少不夠。他睡眠只剩下「兩三個小時,整夜都在想自己沒睡著」,並且「一直覺得自己快瘋掉了。」
fluoxetine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他說,藥物並沒有完全消除他的憂鬱與焦慮,但感覺就像一條護城河。那些掠食性的情緒多半被擋在水的另一邊,吊橋也被拉了起來。對女友的性慾減弱了,勃起變得不那麼穩定,達到高潮也困難許多,但他部分把這歸因於自己身處一段長期關係。當他最後決定停藥,想試著在不靠藥物的情況下面對焦慮時,勃起能力恢復了,高潮也不再那麼困難。之後,當他結束這個不服藥的實驗,重新回到fluoxetine時,性方面的困難也一併回來。那條護城河一方面將讓人癱瘓的焦慮擋在外面,另一方面也常常讓勃起與高潮保持在遠處。
當我問他是否擔心PSSD時,他猜自己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畢竟他在停藥那段期間曾重新找回性。然而,從我們的對話中看來,他似乎並不太在意,隨著服藥年數逐年累積,他在長期上可能面臨什麼樣的風險——儘管「有時候很難維持勃起或一開始就勃起」,也儘管「得剛好星星排好隊」他才有辦法達到高潮。對他來說,他說,fluoxetine「效果超好」。他願意承受性方面的代價。他會告訴伴侶:「下面有時候會有點怪。」他說,「尤其是在New York」這樣的地方,他現在就住在那裡,「很多人都在吃或曾經吃過S.S.R.I.,所以大家都滿能理解。」
和True一樣,Sami的故事也談到需要用藥,但她的故事同時也關乎悔意。Sami自13歲起就有憂鬱的歷史。那時,她開始用獵刀割傷自己。在心理治療、運動與新朋友的幫助下,沒有用藥,她把自己從那口井裡爬了出來。但在大學畢業後三年,她在一段感情結束後再度陷入憂鬱。一位心理治療師轉介她去找家庭科醫師,後者為她開了sertraline,也就是Zoloft的學名藥。她說,這藥「的確把我從那口井裡拉了出來。」
但她很快注意到,在用藥期間,高潮變得「很膚淺」、而且「轉瞬即逝」,她回憶道。「那讓性這件事裡主導的情緒變成挫折。」她服藥略多於一年,停藥至今已經六年。真正讓她完全沈浸其中的性愛,多半仍停留在過去,她也擔心那會永遠留在過去,儘管她告訴我,她覺得那種能力現在「正以滴漏般的速度回來。」她承認,當初決定嘗試用藥時,「我覺得自己已經別無選擇,而藥物真的幫了我。」然而她說,如果當時知道自己現在相信是長期副作用的這些事,「我會更認真思考。」她說:「我很想念自己在S.S.R.I.之前的身體。」
對Guin來說,當初用藥並非急迫必要。為了治療憂鬱,一名精神科醫師在她17歲時替她開了標準劑量的Celexa。她並不確定自己需要用藥,但她說:「那時候我非常乖,很順從。」她很快注意到,自己的性衝動被「調暗」了。在那之前,她記得,「我想高潮時很容易就能達到。我是個有性慾的人,只是還沒和任何人分享過那一部分。」她回想起12歲時對鄰居男孩的早期迷戀,那男孩大她約四歲。「我會和他的小妹妹們一起玩,有時候他會加入我們,一起翻跟斗之類的。我會一直想著他。我一定會在附近遊走,等著他放學走過來。」
在大學期間,她在戀愛關係中掙扎,而她把這和藥物的性副作用連結在一起。23歲時,她開始逐漸停藥,希望找回被削弱的性。結果卻發現自己「完全被去情色化」,她說。她上網搜尋,讀到PSSD的討論與可能永久的說法。「我心想:我毀了自己的人生。我摧毀了自己擁有正常關係的能力。前幾年裡,我每天早上醒來都會想起這件事,想到這就是我的現實,我只想回去睡覺再也不要醒來。我常常想到自殺。」
她去看醫師,醫師說她的症狀是憂鬱復發。他們說:「有些人會說,他們覺得自己的性沒有心理健康那麼重要。」這些否定讓她感到羞愧。
距離Guin停用S.S.R.I.已經六年。她今年29歲。「我沒有談戀愛的能力,」她說。「那部分就以一種非常鮮明的方式消失了。對我而言,浪漫的化學反應與性之間的連結實在太深了,浪漫不可能在性之外獨立存在。」她不期待自己的狀況會有改變。「我之所以在心理上稍微好一些,是因為我學會忍受一個新的正常。」
她剛生下第一個孩子。因為沒有伴侶,她選擇了試管受精。「我曾經想要一個伴侶,」她說。「我希望孩子是在媽媽與爸爸都在的環境下長大。當你想到大多數長期關係都建立在性關係上,你的性生活就變得非常核心。」她解釋說:「即使我對當父母感到興奮,我還是會不時被一陣新的悲傷擊中。我不得不走到這一步,我的人生竟然變成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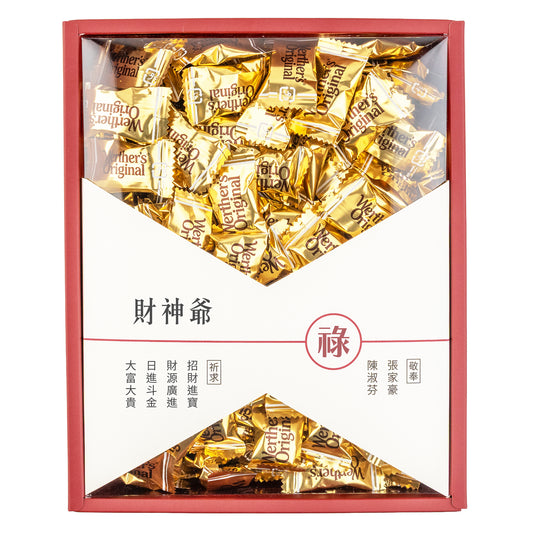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