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亞里斯多德到尼采:尋找人生意義的哲學思考
Share
許多哲學上的重要歷史人物都對「什麼使生命變得有意義」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雖然他們通常不是以這樣的方式提出(關於這種討論只在大約250年前開始,請參見Landau 1997)。例如,亞里斯多德談到人的功能,阿奎那談到至福視界,康德談到最高善。相關的,想想Koheleth,這位被推測為聖經《傳道書》的作者,他描述生命為「虛無」並且像是「追逐風」,尼采談到虛無主義,以及叔本華談到當我們實現了長期渴望的目標時,我們會發現「它是多麼的虛無和空洞」。雖然這些觀點對於幸福和美德(及其對立面)有一定的關聯,但它們可以直接地(大致上)被構建為關於一個人應該實現哪些高度評價的目標才能使她的生命顯得有意義(如果有的話)。
儘管有著古老的血統,但直到大約1980年代,生命的意義才在英美澳大利亞哲學中建立起一個獨特的領域,本篇調查聚焦於此,並且直到過去20年,才出現了具有真正深度和複雜性的辯論。二十年前,關於生命意義的分析反思被描述為相比於幸福或良好品格的討論是一個「邊緣地帶」,在給定的對該領域的批判性討論中幾乎可以引用全部文獻(Metz 2002)。這已不再是事實。英美澳大利亞的生命意義哲學變得充滿活力,以至於現在有太多的文獻無法在這次調查中全面引用。為了獲得焦點,它傾向於討論書籍、有影響力的論文和更近期的作品,並將來自其他哲學傳統(如大陸或非洲)和非哲學領域(例如,心理學或文學)的貢獻擱置一旁。這次調查的核心目標是讓讀者熟悉當前分析生命意義的方法,概述主要辯論並指出值得進一步考慮的被忽視主題。
當提及生命的意義時,人們傾向於提出三個問題之一:「你在談論什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以及「生命實際上有意義嗎?」。由從事分析傳統工作的人所撰寫的生命意義文獻(本條目聚焦於此)可以根據它試圖回答哪個問題來有用地組織。這次調查從最近的工作開始,這些工作處理第一個抽象的(或“元”)問題,關於“生命的意義”的談話的意義,即,旨在澄清我們在探究生命意義時心中所想(第1節)。之後,它考慮提供對更實質性問題——意義本質的回答的文本(第2-3節)。正在形成一個應用意義的子領域,與應用倫理學平行,在特定案例或特定主題的背景下考慮意義。例子包括減壓(Levy 2005)、實施遺傳增強(Agar 2013)、取得成就(Bradford 2015)、獲得教育(Schinkel et al. 2015)、與研究參與者互動(Olson 2016)、勞動自動化(Danaher 2017)和創造孩子(Ferracioli 2018)。相比之下,這次調查幾乎專門關注當代規範理論上對生命意義的方法,即,嘗試用一個單一的、通用的原則捕捉所有可能賦予生命意義的多種條件。最後,這次調查檢視了新的論證,支持虛無主義觀點,即賦予任何人生命意義所需的條件並不存在,亦即,我們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無意義的(第4節)。
1. 「意義」的意義
該領域的目標之一包括系統性地嘗試確定人們(本質上或特徵性地)在思考生命意義這個主題時心中所想的是什麼。對許多從事此領域研究的人來說,「重要性」和「意義」這樣的詞語是「有意義性」的同義詞,因此無法揭示足夠的信息,但也有一些人在有意義性和意義之間劃分界限(Singer 1996, 112–18; Belliotti 2019, 145–50, 186)。關於一個無意義生活的概念如何關聯到荒謬(Nagel 1970, 1986, 214–23; Feinberg 1980; Belliotti 2019)、徒勞(Trisel 2002)和不值得活的生活(Landau 2017, 12–15; Matheson 2017)的想法,也存在辯論。
開始澄清關於思考生命意義所涉及的是指定承載者的一個有用方法。詢問者心中想的是哪一種生活?一個標準的區分是在於生命「中」的意義,即一個人類個體是可以展示意義的,以及狹義的生命「的」意義,即人類整體是可以有意義或沒有意義的。最近也有一些考慮動物或人類嬰兒是否可以在他們的生活中擁有意義,大多數人拒絕這種可能性(例如,Wong 2008, 131, 147; Fischer 2019, 1–24),但也有少數人開始為此提出案例(Purves and Delon 2018; Thomas 2018)。同樣未被充分探索的問題是,如一個民族或一個組織這樣的群體是否可以是意義的承載者,如果可以,是在什麼條件下。
大多數分析哲學家對生命中的意義感興趣,即一個人的生活可能展示的有意義性,相比之下,如今很少有人處理狹義的生命意義。即使是那些相信上帝是或將是生命意義的核心的人,近來也更多地討論個體生活如何因上帝而有意義,而不是討論人類種族可能如何有意義。儘管一些人認為,就其本身而言,人類生活的有意義性值得研究不亞於(如果不是更多的話)生活中的意義(Seachris 2013; Tartaglia 2015; 參見Trisel 2016),但大多數領域的研究者反而對他們作為個體人(以及他們關心的那些人的生活)是否有意義以及如何能變得更有意義感興趣。
聚焦於生命中的意義,普遍的看法是,它在概念上是為其自身的善而存在的東西,或者相關地,是為行動提供基本理由的東西(關於此,見Visak 2017)。近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一個人的生活中可以存在中性或甚至不希望的意義類型(例如,Mawson 2016, 90, 193; Thomas 2018, 291, 294)。然而,這些是異端,大多數分析哲學家,和大概的普通人,反而想知道何時一個人的生活展示了某種終極價值(或非工具性行動理由)。
另一個有大量共識的主張是,有意義性不是全有或全無,而是有程度之分,這樣某些生活時期比其他時期更有意義,有些人的整個生活比其他人的更有意義。注意,一個人可以一貫地持有這樣的觀點:某些人的生活比其他人的生活意義較少(或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較“不重要”),或者甚至是無意義的(不重要的),並且仍然認為所有人從道德角度來看有平等的地位。考慮一個根據結果主義道德原則,每個個體因為具有有意義生活的能力而計算為一,或者一個康德式的方法,根據這個方法,所有人因為他們自主決策的能力而擁有尊嚴,其中意義是這種能力行使的一種功能。對於這兩種道德觀點,我們可能被要求幫助那些生活相對無意義的人。
關於個人有意義性概念的另一個相對無爭議的要素是,它與幸福或正確性(在Wolf 2010, 2016中強調)邏輯上是獨立的。首先,問某人的生活是否有意義,並不與問她的生活是否愉快或她是否主觀上過得好相同。在體驗機器或虛擬現實設備中的生活肯定是一個快樂的生活,但很少有人認為它是有意義性的初步候選(Nozick 1974: 42–45)。事實上,有些人會說,一個人的生活可以通過犧牲自己的幸福來獲得意義,例如,為了幫助他人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其次,問一個人隨著時間的存在是否有意義,與考慮她是否道德上正直不同;直覺上有增強意義的方式與正確行為或道德美德無關,比如做出科學發現或成為一位優秀的舞者。現在,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如果一個生活是不快樂或不道德的,那麼它就是無意義的,但那將是設定一個合成的、實質性的關係,而不是表示談論「有意義性」在分析上就是關於幸福或正確性的想法。
假設「生命中的意義」意味著某種為其自身的善而存在的東西,可以有程度差異,且與幸福或正確性在分析上不等同,那麼它還涉及什麼?我們還能說些什麼關於這個終極價值的定義呢?大多數當代分析哲學家會說,相關的價值不會出現在體驗機中度過的時間裡(但見Goetz 2012對不同觀點的討論)或像西西弗斯這樣的神話人物的生活中,西西弗斯被希臘神明註定永遠在山上滾動一塊石頭(由Albert Camus和Taylor 1970著名討論)。此外,許多人會說,相關的價值典型地由「善、真、美」的經典三位一體所體現(或在某些條件下體現)。這些術語不應該被字面上理解,而是粗略地代表了仁愛關係(愛、同事情誼、道德)、智慧反思(智慧、教育、發現)和創造性(特別是藝術,但也可能是像幽默或園藝這樣的事物)。
更進一步,善、真、美的價值和任何其他可能的意義來源涉及的是什麼?目前在該領域還沒有共識。一個突出的觀點是,生命中意義的概念是一組或混合物的重疊想法,如實現更高層次的目的、贏得重大的尊重或欽佩、具有顯著的影響、超越自己的動物本性、使事物有意義或展示一個引人入勝的生活故事(Markus 2003; Thomson 2003; Metz 2013, 24–35; Seachris 2013, 3–4; Mawson 2016)。然而,也有哲學家堅持認為關於概念有更單一的真理,因此(幾乎)所有關於個體生活中有意義性的思考本質上都是關於單一屬性。建議包括致力於或對質量上優越的善感到敬畏(Taylor 1989, 3–24)、超越自己的限制(Levy 2005)或做出貢獻(Martela 2016)。
最近該領域出現了某種“解釋性轉向”,其中一個例子是強烈的觀點,即談論意義在邏輯上關於生活是否以及如何在更廣泛的參考框架內具有可理解性(Goldman 2018, 116–29; Seachris 2019; Thomas 2019; 參見Repp 2018)。根據這種方法,探究生命的意義就是尋找使事物有意義的信息,也許是關於生活的敘事或其來源和命運的解釋。這種分析的優勢在於它承諾將“意義”一詞的廣泛用法統一起來。然而,它的缺點是無法捕捉到這樣的直覺:生命中的意義本質上是為其自身的善(Landau 2017, 12–15),維持一種無法言喻的條件賦予生命意義並不邏輯上矛盾(如Cooper 2003, 126–42; Bennett-Hunter 2014; Waghorn 2014所述),以及經常是人類行為本身(與其解釋不同),如從燃燒的大樓中救出一個孩子,是賦予意義的事物。
一些思想家提出,對生命的意義概念的完整分析應該包括所謂的“反物質”(Metz 2002, 805–07, 2013, 63–65, 71–73)或“反意義”(Campbell and Nyholm 2015; Egerstrom 2015),這是減少生命有意義性的條件。這種想法是,意義最好被表示為一個雙極尺度,其中不僅有正面條件,還有負面條件。無端的殘酷或破壞性行為是減少一個人生活可能擁有的意義的首要候選行為。
儘管對如何分析生命的意義概念(或闡述“生命中的意義”短語的定義)進行了持續的辯論,這個領域仍處於良好的位置,可以在上面提出的其他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即什麼會使生活有意義以及是否有任何生活實際上是有意義的。一定程度的共同基礎是由這一點提供的:有意義性至少涉及一個人生活中的梯度終極價值,這與幸福和正確性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其典範可能是善、真、美。接下來的討論將關注哲學上試圖理論性地捕捉這種價值的本質,以及確定它至少在我們一些人的生活中是否存在。
2. 超自然主義
大多數關於生命意義的分析哲學家一直在試圖開發和評估理論,即旨在捕捉所有可能賦予生命意義的特定方式的基本和普遍原則。如同道德哲學一樣,存在可識別的「反理論主義者」,即那些認為意義條件之間存在過多多元性,無法以原則的形式統一它們的人(例如,Kekes 2000; Hosseini 2015)。然而,可以論證,系統性尋求統一的努力仍然太初級,無法就其可行性作出堅定結論。
這些理論通常基於形而上學的劃分,即根據哪些種類的性質被認為構成了意義。超自然主義理論是認為精神領域對生命意義至關重要的觀點。大多數西方哲學家將精神理解為在亞伯拉罕諸信仰中通常理解的上帝或靈魂(但見Mulgan 2015關於一個對我們不感興趣的上帝在意義上下文中的討論)。相反,自然主義理論是認為特別是科學方法非常了解的物理世界對生命的意義至關重要的觀點。
邏輯上存在非自然主義理論的空間,根據該理論,意義的核心是既非精神也非物理的抽象性質。然而,近期的英美澳大利亞文獻中僅略微關注了這種可能性(Audi 2005)。
值得注意的是,超自然主義——聲稱上帝(或靈魂)會賦予生活以意義——在邏輯上與有神論——聲稱上帝(或靈魂)存在——是不同的。雖然大多數持超自然主義的人也持有神論,但一個人可以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後者(正如加繆或多或少所做的),這讓人認為生活是無意義的或至少缺乏重大意義。同樣,雖然大多數自然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維持上帝存在但與生命意義無關,或者甚至減損生命意義的觀點並不矛盾。雖然這些立場組合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其中一些可能在實質上不合理。這個領域可以從討論關於什麼會賦予生活意義的各種評價聲明和關於精神條件是否存在的形而上學聲明的相對吸引力中受益。
在過去的15年左右,超自然主義在定期基礎上被區分為兩種不同類型(Metz 2019)。這不僅在生命意義的文獻中是真實的,也在相關的親神論/反神論辯論中是真實的,關於上帝或靈魂存在是否是可取的(例如,Kahane 2011; Kraay 2018; Lougheed 2020)。一方面,有極端的超自然主義,根據這種觀點,精神條件對任何生命意義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上帝或靈魂,那麼根據這種觀點,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無意義的。另一方面,有溫和的超自然主義,根據這種觀點,精神條件對偉大或終極的生命意義是必要的,儘管不是對生命意義本身而言。如果沒有上帝或靈魂,那麼根據這種觀點,每個人的生活都可能有某些意義,甚至是有意義的,但沒有人的生活可以展現最理想的意義。對於一個溫和的超自然主義者來說,上帝或靈魂會大幅增強有意義性或是其主要貢獻條件。
偉大或終極意義已被以多種方式描述,有時是量化地作為「無限」(Mawson 2016),質化地作為「更深」(Swinburne 2016),關係性地作為「無限的」(Nozick 1981, 618–19; 參見Waghorn 2014),時間性地作為「永恆的」(Cottingham 2016),以及從宇宙的角度來看(Benatar 2017)。關於這些區別如何影響彼此的關鍵問題尚未反思,例如,是否有些比其他更基本,或有些比其他更有價值。
極端/溫和的區分交叉的是基於上帝理論和基於靈魂理論的區別。根據前者,某種與上帝(被理解為一個全知、全善、全能的精神人格,是物理宇宙的基礎)的聯繫構成生命意義,即使一個人缺少靈魂(被構想為一種包含一個人身份的不朽的精神實質)。相反,根據後者,擁有一個靈魂並將其置於某種狀態是使生活有意義的原因,即使上帝不存在。許多超自然主義者當然認為上帝和靈魂對於(非常)有意義的存在是聯合必要的。然而,僅需其中之一是必要的這個更簡單的觀點很常見,有時為復雜觀點提供的論據並不比為簡單觀點提供更多的支持。
2.1 以上帝為中心的觀點
關於生命意義的最有影響力的基於上帝的說法是極端觀點,即一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如果且僅如果一個人實現了上帝指派的目標。熟悉的想法是,上帝對宇宙有一個計劃,且一個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上帝實現這一計劃就有多大程度的意義,也許是以上帝希望某人以特定方式做的方式。如果一個人未能做上帝意圖她用她的生活做的事情(或者如果上帝甚至不存在),那麼根據當前的觀點,她的生活將是無意義的。
思想家們對於上帝的目的之所以可能獨特地賦予人類生命以意義有不同的看法,但最有影響力的論點是,只有上帝的目的可以是不變的道德規則的來源(Davis 1987, 296, 304–05; Moreland 1987, 124–29; Craig 1994/2013, 161–67)或更一般地是客觀價值的來源(Cottingham 2005, 37–57),缺乏這樣的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毫無意義。根據這個論點,像動物的快樂或慾望滿足這樣的低級善可以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存在,但與生命意義有關的更高級善,特別是道德美德,則不行。然而,批評者指出許多非道德的生命意義來源(例如,Kekes 2000; Wolf 2010),有一位論者認為,即使說,仁慈行為是必要的,一個普遍的道德準則也不是生命意義所必需的(Ellin 1995, 327)。此外,如今提供了各種自然主義和非自然主義的客觀道德賬戶,以及更一般的價值賬戶,因此並不清楚它必須有上帝意志中的超自然來源。
對於上帝的目的可能使生活有意義的想法的一個反復出現的反對意見是,如果上帝創造了我們並考慮到一個目的,那麼上帝就會降低我們,從而削弱我們從實現這一目的中獲得意義的可能性。這一反對意見追溯到讓-保羅·薩特,但在分析文獻中,似乎是庫爾特·拜爾首次闡述它(1957/2000, 118–20; 參見Murphy 1982, 14–15; Singer 1996, 29; Kahane 2011; Lougheed 2020, 121–41)。有時關注點是上帝將發出的威脅懲罰,以使我們執行上帝的命令,其他時候是意義的來源是限制性的並不取決於我們,還有時候是僅僅通過被創造出來並賦予某種目的,我們的尊嚴就會受到貶低(關於對這些擔憂的一些回應,見Hanfling 1987, 45–46; Cottingham 2005, 37–57; Lougheed 2020, 111–21)。
對於一個極端基於上帝的觀點,有一個不同的論點,它較少關注上帝作為有目的性的,更多關注上帝作為無限、無限制或難以言喻的,羅伯特·諾齊克首次小心地闡述了這一點(Nozick 1981, 594–618; 參見Bennett-Hunter 2014; Waghorn 2014)。核心想法是,對於一個有限的條件來說,要想有意義,就必須從另一個有意義的條件中獲得其意義。因此,如果一個人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它可能是因為與一個重要的人結婚。作為有限的,配偶必須從其他地方獲得他或她的重要性,也許是從他或她所做的工作類型中獲得。這項工作也必須通過與其他有意義的東西相關來獲得其意義,依此類推。存在一個關於有意義條件的回歸,建議是這種回歸只能在某個如此全面以至於不需要(實際上,不能)從任何其他東西中獲得意義的東西中終止。那就是上帝。對這種關係理由的標準反對是,一個有限的條件可以有意義,而不需要從另一個有意義的條件中獲得其意義。也許它本身就有意義,而不需要與它之外的東西相連,或者也許它可以通過與某個美麗的或以其他方式為自身價值而有價值的東西相關來獲得其意義,但不是有意義的(Nozick 1989, 167–68; Thomson 2003, 25–26, 48)。
對於任何極端基於上帝的觀點而言,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明顯的反例存在。如果我們想到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特蕾莎修女和巴勃羅·畢卡索的典型生活,即使我們假設沒有全知、全能、全善的精神人格作為物理世界的基礎,它們似乎也是有意義的(例如,Wielenberg 2005, 31–37, 49–50; Landau 2017)。即使是宗教傾向的哲學家這些天也發現很難否認(Quinn 2000, 58; Audi 2005; Mawson 2016, 5; Williams 2020, 132–34)。
大多數因這個原因,當代的超自然主義者傾向於選擇溫和性,即維持上帝會大大增強我們生活中的意義,即使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中也可能有一些意義。一種方法是利用關係論證來顯示上帝是必要的,不是對任何意義都是必要的,而是對終極意義是必要的。"有限的超越性,超越我們的限制以連接到一個更廣闊的價值背景,這本身是有限的,確實賦予了我們的生活以意義——但是一個有限的。我們可能渴望更多"(Nozick 1981, 618)。另一個角度是呼籲在上帝的計劃中扮演角色,再次聲稱,不是對意義本身是必要的,而是對"宇宙意義....而不是時間和空間非常有限的意義"(Swinburne 2016, 154; 參見Quinn 2000; Cottingham 2016, 131)。另一種理由是,通過實現上帝的目的,我們會有意義地取悅上帝,一個完美的人,並將永遠被上帝記得(Cottingham 2016, 135; Williams 2020, 21–22, 29, 101, 108)。還有一個論點是,只有有了上帝,人性的最深層欲望才能得到滿足(例如,Goetz 2012; Seachris 2013, 20; Cottingham 2016, 127, 136),即使更表層的欲望可以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得到滿足。
對於溫和超自然主義的這些理由的回應中,有一種建議是,正是因為在宇宙中獨自一人,我們的生活才會特別有意義;否則,上帝的偉大會使我們黯然失色(Kahane 2014)。還有一種回應是,隨著來自上帝的更大意義的機會,也會有更大的反意義的風險,所以不清楚有上帝的世界是否會在意義方面提供凈增益(Metz 2019, 34–35)。例如,如果取悅上帝會大大增強我們生活的意義,那麼大概不取悅上帝也會以相當程度減少它。此外,下面(第3.3小節)提到的對極端自然主義(或其「反神論」表親)的論證也值得討論。
2.2 以靈魂為中心的觀點
上述為超自然主義辯護的論點中,沒有一個(至少不是明確地)訴諸於永恆生命的前景。那些確實訴諸於此的論點是以靈魂為中心的,認為生命意義主要來自於擁有一個不朽的、精神的實質,該實質在人活著時與其身體相連,並將永遠活過其死亡。有些人將來世想象為自己的靈魂進入一個超凡的、精神的領域(天堂),而其他人則想象自己的靈魂在地球上轉生到另一個身體中。根據極端版本,如果某人有靈魂但未能將其置於正確狀態(或如果某人完全缺乏靈魂),那麼其生活是無意義的。
支持極端以靈魂為基礎觀點的三個主要論點。一個由列夫·托爾斯泰使之聞名的論點是,為了讓生活有意義,必須有值得做的事情,而只有在它對世界產生永久影響的情況下,事情才值得做,而產生永久影響則需要不朽(參見Hanfling 1987, 22–24; Morris 1992, 26; Craig 1994)。批評者通常訴諸反例,例如,即使你和他們都是凡人,幫助防止人們受苦無疑是值得你的時間和努力的。事實上,有些人已經反擊並辯稱,只有當且因為他們是凡人,幫助人們才值得犧牲,否則他們總能在來世中獲得補償(例如,Wielenberg 2005, 91–94)。另一個最近且有趣的批評是,聲稱如果有一天一切都將結束,那麼現在沒有什麼重要的主要動機是不合理的(Greene 2021)。
認為沒有靈魂生活將無意義的第二個論點是,為了實現正義,這又是生命有意義所必需的,靈魂是必要的。當邪惡者昌盛而義人受苦時,生活似乎是無意義的,至少假設沒有其他世界可以糾正這些不公正,無論是通過上帝還是因果報應力量。《傳道書》中可以找到這樣的論點,它繼續被辯護(例如,Davis 1987; Craig 1994)。然而,即使承認來世對於完美的公正結果是必需的,永恆的來世對它們來說是必需的遠非顯而易見,然後,有人建議,像曼德拉這樣的生活,正是因為遇到不公正並與之抗爭才變得有意義。
認為擁有靈魂對任何意義都是必要的第三個論點是,它對於我們擁有的那種自由意志是必要的,沒有這種自由意志,我們的生活將是無意義的。伊曼紐爾·康德以認為如果我們僅僅是物理存在,受自然法則的約束,就像物質世界中的其他一切一樣,那麼我們就不能出於道德原因行動,因而我們將是無足輕重的。近期,一位神學家以宗教術語優雅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道德精神在選擇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它在源自人類並與其作為其內在本質保持的那些東西中找到,而不是在外在條件的偶然性或運氣的轉折中找到……(當)任何人激活他的道德良知時,一個精神確實會出現。這個精神就是上帝……在上帝的‘你必須’和人的‘我能’中包含了上帝在人生中的神聖形象”(Swenson 1949/2000, 27–28)。注意,即使道德規範不源於上帝的命令,這種論證的邏輯意味著,只要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能力做出道德正確的選擇,他的生活就可能是有意義的。反過來,這可能需要一個人的自我擁有某種非物質的特質,以克服他可能面臨的任何物理法則和力量。對這種推理的標準反對是提出物理本性被決定和能夠出於道德原因行動的兼容論(例如,Arpaly 2006; Fischer 2009, 145–77)。同時,值得探討的是,如果要擁有自由選擇的精神本質,是否必須是永不消逝的。
如同以上帝為中心的理論家一樣,許多以靈魂為中心的理論家如今也採取溫和的觀點,接受即使沒有不朽,生命中也會有一定的意義,但主張擁有它將會帶來更大的意義。承認愛因斯坦、曼德拉和畢卡索的生活在沒有經歷身體死亡的存續中仍具有一定意義(例如,Trisel 2004; Wolf 2015, 89–140; Landau 2017),仍存在一個強有力的想法:更多總是更好。如果有限的生活因擁有善、真、美而在某種程度上有意義,那麼如果它展現這些更高價值——包括與上帝的關係——永遠地,無疑會擁有更多的意義(Cottingham 2016, 132–35; Mawson 2016, 2019, 52–53; Williams 2020, 112–34; 參見Benatar 2017, 35–63)。對這種推理的一個反對是,擁有靈魂可能的意義無窮大,讓溫和超自然主義者難以解釋愛因斯坦等有限生活的意義確實可以與之相比(Metz 2019, 30–31; 參見Mawson 2019, 53–54)。更常見的是,反對認為永恆生活會包括各種反意義,如厭倦和重複,在極端自然主義的背景下討論(第3.3小節)。
3. 自然主義
回想一下,自然主義是這樣一種觀點:物理生活對生命的意義至關重要,即使沒有精神領域,也可能有一個極其有意義的生活。像超自然主義一樣,當代自然主義承認有兩種可辨識的變體:溫和型和極端型(Metz 2019)。溫和版本是,雖然在一個純粹由科學很好地了解的物理宇宙中可以擁有一個真正有意義的生活,但如果存在一個精神領域,則可能有一個更有意義的生活。上帝或靈魂可以增強生命的意義,儘管它們不會是主要貢獻者。自然主義的極端版本是認為,如果沒有精神領域,對生命的意義而言會更好。從這個角度來看,上帝或靈魂將是反物質,即會減損我們可得到的意義,使一個純粹的物理世界(即使不是這個特定的世界)更為可取。
溫和/極端區分的交叉是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之間的區別,這些是關於意義的本質的理論賬戶,因為它是物理的。它們在人類心靈在多大程度上構成意義以及是否存在對所有人類不變的意義條件方面有所不同。主觀主義者相信沒有不變的意義標準,因為意義相對於主體,即取決於個體的親近態度,如她的特定欲望或目標,這不是每個人都共有的。大致上,如果一個人強烈希望某事或打算尋求它,且她獲得了它,那麼對一個人來說某事就是有意義的。客觀主義者則相反認為,存在一些不變的意義標準,因為意義至少部分地獨立於心靈,即不僅僅因為是任何人的心理狀態的對象而獲得。這裡,某事是有意義的(部分地)因為它的內在本質,意味著它獨立於是否被想要或打算;意義相反地(在某種程度上)是應該引起這些反應的那種事物。
3.1 主觀主義
根據這種自然主義的版本,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取決於每個人變化的親近態度。常見的例子是,一個人的生活越能獲得她恰好強烈想要的東西,實現她高度重視的目標,或做她認為真正重要的事,就越有意義(Trisel 2002; Hooker 2008)。一位有影響力的主觀主義者最近堅稱,相關的心理狀態是關心或愛,所以生活的意義正是在於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關心或愛某事(Frankfurt 1988, 80–94, 2004)。另一個最近的提議是,意義在於「一種積極的投入和肯定,使自由創建或接受並現在推動和培養她最關心的項目的人變得生動」(Belliotti 2019, 183)。
主觀主義在二十世紀中葉佔主導地位,當時實證主義、非認知主義、存在主義和休謨主義具有影響力(Ayer 1947; Hare 1957; Barnes 1967; Taylor 1970; Williams 1976)。然而,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四分之一,推理到最佳解釋和反思平衡成為被接受的規範論證形式,經常被用來辯護關於客觀價值存在和本質的主張(或“外部理由”,獨立於現有態度獲得的理由)。結果,關於意義的主觀主義失去了其主導地位。繼續持有主觀主義的人通常對試圖證明關於客觀價值的信念持懷疑態度(例如,Trisel 2002, 73, 79, 2004, 378–79; Frankfurt 2004, 47–48, 55–57; Wong 2008, 138–39; Evers 2017, 32, 36; Svensson 2017, 54)。理論家們接受主觀主義通常是因為替代方案不討喜;他們相當確信一些人的生活是有意義的,但看不出這意義如何能基於心靈獨立的事物上,無論是自然的、超自然的還是非自然的。與這些可能性相比,根據人們發現有意義的事物或人們希望從自己的生活中獲得什麼來解釋有意義的事物似乎很直接。廣泛的元倫理學辯論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和語言哲學中是處理這種主觀主義理由所必需的。
還有一系列更有限的論點支持主觀主義,根據這些論點,這一理論最能解釋生命意義的某些直觀特徵。首先,主觀主義似乎是合理的,因為人們合理地認為一個有意義的生活是一個真實的生活(Frankfurt 1988, 80–94)。如果一個人的生活在她對自己或她的深層本性保持真實的程度上是有意義的,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意義僅僅是那些事物的功能,對於這些事物,這個人在乎。其次,通常認為意義來自於迷失自我,即沉浸在一項活動或體驗中,而不是對它感到厭煩或發現它令人沮喪(Frankfurt 1988, 80–94; Belliotti 2019, 162–70)。集中精神的工作和引人入勝的關係似乎是意義的核心,且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涉及的主觀元素。第三,意義通常被認為是使生活對特定人來說值得繼續的東西,即給她早上起床的理由,這是主觀主義被認為最能解釋的(Williams 1976; Svensson 2017; Calhoun 2018)。
批評者認為,這些論點容易受到一個共同反對的攻擊:它們忽略了在實現自我、迷失自我和有活下去的理由中客觀價值(或外部理由)的作用(Taylor 1989, 1992; Wolf 2010, 2015, 89–140)。一個人如果說,成功維持頭上的3,732根頭髮(Taylor 1992, 36),培養自己在長距離吐痰方面的技能(Wolf 2010, 104),收集一大團繩子(Wolf 2010, 104),或者,吃自己的糞便(Wielenberg 2005, 22),那麼他不是真正對自己保持真實、以有意義的方式迷失自我或擁有真正的生活理由。這些反例表明,主觀條件不足以為生命意義提供基礎;似乎存在某些行為、關係和狀態是客觀有價值的(但見Evers 2017, 30–32),人們的親近態度應當朝向它們,如果要獲得意義的話。
所說的客觀主義者,但主觀主義者感受到這一點的吸引力,通常試圖避免反例,以免他們不得不接受維持頭上的3,732根頭髮等所有這些行為的有意義性(對於一些確實這樣做的人,見Svensson 2017, 54–55; Belliotti 2019, 181–83)。一個重要策略是建議主觀主義者可以通過訴諸於正確類型的親近態度來避免反例。而不是任何個體恰好想要的東西,也許相關的心理狀態是一種情感-感知的看作為狀態(Alexis 2011; 參見Hosseini 2015, 47–66)、一種“範疇”的慾望,即一種構成一個人身份的內在慾望,一個人認為它使生活值得繼續(Svensson 2017),或一個判斷,即一個人有充分理由高度珍視某事物本身(Calhoun 2018)。 即便如此,客觀主義者會辯稱,可能“看起來任何意志選擇視為從事其自身的好理由,對於意志來說,就是一個好理由。但是意志本身......渴望客觀的理由;而且往往除非它認為自己擁有它們,否則它無法前進”(Wiggins 1988, 136)。而且如果不訴諸於客觀性,那麼反例很可能會再次出現。
另一種主觀主義者處理反例的策略是試圖將意義的基礎,不是建立在個體評價者的親近態度上,而是建立在一個團體的親近態度上(Darwall 1983, 164–66; Brogaard and Smith 2005; Wong 2008)。這種互主觀性的轉變是否避免了(更多的)反例?如果是,它是否比客觀理論更可信地這樣做了嗎?
3.2 客觀主義
客觀自然主義者相信,生命意義至少部分由物質世界的某些條件構成,而不僅僅是因為它是親近態度的對象。在這一觀點上,獲得某種情感、慾望或判斷的對象不足以賦予意義。相反,物質世界的某些條件可能賦予任何人的生活以意義,不僅僅因為它們被視為有意義、被自身所需或被認為值得選擇,而是(至少部分地)因為它們本身具有固有的價值或價值。
道德(善)、探究(真)和創造性(美)是廣泛認為能夠賦予生命意義的活動實例,而修剪腳趾甲和吃雪——以及上述對主觀主義的反例——則不是。客觀主義被廣泛認為是這些特定判斷的有力一般解釋:前者之所以有意義,不僅僅是因為某個主體(無論是個體、她的社會,還是上帝)關心它們或判斷它們值得做,而後者簡直缺乏意義,即使有某個主體關心它們或判斷它們值得做也無法獲得意義。從客觀視角看,個體可能關心錯誤的事物或誤以為某事值得,而不僅僅是因為某事她更關心或判斷為更值得選擇。當然,關於價值的存在和本質的元倫理學辯論再次與評價這一理由相關。
一些客觀主義者認為,個人的心理狀態在使該人的生活有意義方面沒有構成作用,儘管他們當然認為它經常發揮工具作用——畢竟,喜歡某種活動很可能激勵一個人去做它。相對較少的客觀主義者是這樣的“純粹”型,儘管結果主義者確實是明顯的例子(例如,Singer 1995; Smuts 2018, 75–99)。大多數客觀主義者反而試圖通過認為一個人的生活因客觀因素更有意義,但也部分因為命題態度如認知、意向和情感,來解釋驅動主觀主義的上述直覺。蘇珊·沃爾夫的混合觀點特別有影響力,她用這句簡練的口號來概括:“當主觀吸引遇到客觀吸引力時,意義就會出現”(Wolf 2015, 112;參見Kekes 1986, 2000;Wiggins 1988;Raz 2001, 10–40;Mintoff 2008;Wolf 2010, 2016;Fischer 2019, 9–23;Belshaw 2021, 160–81)。這一理論意味著,如果一個人相信、滿足於或關心一個並非真正值得的項目,那麼她的生活就不會獲得意義,或者如果一個人從事一個真正值得的項目但未能判斷它重要、對它感到滿足或 關心它,那麼也是如此。另一種相關的方法是,雖然主觀吸引不是必需的,但它可以增強意義(例如,Audi 2005, 344; Metz 2013, 183–84, 196–98, 220–25)。例如,一位因她的大量慈善工作而感到無聊且疏遠的典型特蕾莎修女可能因此而擁有一個有些意義的存在,即使如果她對此感到自豪或認同它,她的存在將會更有意義。
已有幾次試圖理論上捕捉所有客觀吸引力、固有價值或終極價值條件共有的特徵,就其對個人生命的意義影響而言。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遇到的提議包括:客觀有意義的條件僅是那些涉及積極連接超越自我的有機統一(Nozick 1981, 594–619);創造性(Taylor 1987; Matheson 2018);過情感生活(Solomon 1993; 參見Williams 2020, 56–78);促進好的後果,例如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質量(Singer 1995; Audi 2005; Smuts 2018, 75–99);以優異的方式行使或培養理性本性(Smith 1997, 179–221; Gewirth 1998, 177–82; Metz 2013, 222–36);朝著因為接近它們時對它們的了解改變而永遠無法完全實現的目標前進(Levy 2005);實現具有持久時間和廣泛範圍的超越目標(Mintoff 2008);過德行生活(May 2015, 61–138; McPherson 2020);以及愛值得愛的事物(Wolf 2016)。領域內尚未就一個或一小群這些賬戶達成共識。
上述自然主義理論的一大特點是它們是累加或加法式的,令人反感地將生活僅僅視為有意義生活片段的“容器”,這些片段被孤立地考慮時是有意義的(Brännmark 2003, 330)。哲學家對生命意義的討論,特別是客觀主義者,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整個生活,或至少它的長時間段,可以在超越其部分的意義量(如果有的話)方面顯著影響其意義。
例如,一個生活中有很多仁慈和其他直觀賦予意義的條件,但也極度重複的生活(類似於電影《雲裡霧裡》)是不是最大程度上有意義的(Taylor 1987; Blumenfeld 2009)。此外,一個不僅避免重複而且以大量有意義(或其他可取)部分結束的生活似乎總體上比擁有相同數量的有意義(可取)部分但以很少或沒有這些部分結束的生活更有意義(Kamm 2013, 18–22; Dorsey 2015)。還有,在其無意義(或其他不可取部分)通過個人成長過程引發其有意義(可取)部分的生活,似乎因這種救贖模式、"好的人生故事"或敘事自我表達而具有意義(Taylor 1989, 48–51; Wong 2008; Fischer 2009, 145–77; Kauppinen 2012; May 2015, 61–138; Velleman 2015, 141–73)。這三個案例表明,意義可以存在於整個生活中,即存在於其部分之間的關係中,而不僅僅是在孤立考慮的部分中。然而,一些人會認為,嚴格來說,重要的是可以講述一個人生活的故事,而不是生活故事本身即事件之間的關係(de Bres 2018)。
文獻中存在純粹或極端的整體主義版本,根據這些版本,生命意義的唯一可能載體是一個人的整個生活,而不是任何孤立的活動、關係或狀態(Taylor 1989, 48–51; Tabensky 2003; Levinson 2004)。支持這一立場的一個突出論點是,對某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有意義性判斷僅是暫時的,會根據它們如何融入更寬闊的視角而有所修正。因此,例如,最初看來,從瘋子手中拿走斧頭從而保護無辜者似乎為某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些意義,但當人們得知這樣做的意圖僅僅是為了偷斧頭,而不是救命,或者瘋子隨後拿出機關槍造成的傷害比他的斧頭會更大時,人們可能會修改這種判斷。值得考慮這種情況是否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廣,如果能夠,那麼是否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只有整個生活才能展現意義。
或許大多數客觀主義者至少在反思後會接受生活的部分和生活部分之間的整體關係都可以展示意義。假設生活中存在兩種意義的載體,就會出現重要問題。一個問題是,某個敘事是否可以在其部分沒有意義的情況下仍然有意義,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部分是有意義的整體的一部分,那麼該部分的意義是否會增加(關於此,見Brännmark 2003),第三個問題是,如果必須在部分與整體之間做出選擇的情況下,是否有什麼有啟示性的說法關於如何在它們之間進行權衡(Blumenfeld 2009似乎賦予整體以絕對優先權)。
3.3 拒絕上帝和靈魂
自然主義者直到最近一直主要關注於表明沒有上帝或靈魂也能使生命有意義;他們沒有花太多時間考慮這些精神條件如何可能增強意義,而是傾向於以溫和的方式保留這種可能性(Hooker 2008是一個例外)。然而,最近出現了一種極端形式的自然主義,根據這種觀點,如果有上帝或靈魂,我們的生活可能會,如果不是必然的話,至少在意義上會比沒有這些存在的世界少。儘管Baier(1957)早期就表達了這種“反神論”立場,但實際上是在過去十年左右,這一立場才被廣泛且複雜地討論。
一個理由,如前所述作為對上帝的目的構成生命意義的觀點的反對意見,也被用來論證上帝的存在本身將必然降低意義,即將包含反物質。這是關於單一神教傳統中如此突出的主人/僕人和父母/子女的隱喻揭示了我們在存在一個質量更高的、以某種目的創造我們的存在的世界中的地位:我們作為成年人的獨立性或尊嚴會被侵犯(例如,Baier 1957/2000, 118–20; Kahane 2011, 681–85; Lougheed 2020, 121–41)。對這種推理的一個有趣反駁是接受上帝的存在與從屬於自己的老闆所獲得的那種意義(大致說來)不相容,但要爭辯說,上帝也會使更大類型的意義可用,為我們提供凈增益(Mawson 2016, 110–58)。
另一個認為上帝會減損生命意義的主要論點訴諸於隱私的價值(Kahane 2011, 681–85; Lougheed 2020, 55–110)。上帝的全知將不可避免地使我們無法控制其他人對我們最私密細節的訪問,對一些人來說,這等同於比擁有這種控制的生活更少意義的生活。除了質疑我們對上帝隱私的價值外,一種引人深思的批評是建議,如果缺乏隱私真的會大幅度減少我們生活的意義,那麼上帝,作為道德完美的人,會簡單地避免了解我們的一切(Tooley 2018)。缺乏對我們心理狀態的完全了解將與將上帝描述為“全知”的相容,因為只要道德上允許,上帝就擁有盡可能多的知識。
轉向認為擁有靈魂會減少生命的意義的主要論點,因此如果一個人想要一個最大程度上有意義的生活,一個人應該偏好一個純粹的物理世界,或至少是一個人們是凡人的世界。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有論點認為不朽的生活無法避免變得乏味(Williams 1973),根據許多主觀和客觀理論,這會使生活變得毫無意義。關於這個話題的文獻已經非常龐大,中心回應是不朽不必導致乏味(關於最近的討論,見Fischer 2009, 79–101, 2019, 117–42; Mawson 2019, 51–52; Williams 2020, 30–41, 123–29; Belshaw 2021, 182–97)。然而,也許值得質疑乏味是否足以導致無意義。假設,例如,一個人自願無聊,以便讓許多其他人不無聊;或許這會是一個有意義的犧牲。對於永恆無聊肯定不會是幸福或滿足,但如果它能防止其他人永恆無聊,會不會有意義(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如果,如常見的觀點,犧牲自己的生命可能是有意義的,那麼犧牲自己的活力為什麼不可以呢?
反對永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會變得重複,這將大大消耗其意義(Scarre 2007, 54–55; May 2009, 46–47, 64–65, 71; Smuts 2011, 142–44; 參見Blumenfeld 2009)。如果,正如看起來的那樣,在永恆中只有有限數量的行動可以執行、關係可以擁有、狀態可以處於,那麼最終必須重複做同樣的事情。即使一個人的活動可能比永遠推一塊石頭上山(像西西弗斯那樣)更有價值,但永遠重複做它們的前景對許多人來說是令人沮喪的。可以肯定,一個人可能不記得之前做過它們,因此可以避免乏味,但對一些哲學家來說,這會使情況更糟,類似於患有失智症且忘記自己已經講過相同的故事。然而,其他人仍然認為這樣的生活有意義(例如,Belshaw 2021, 197, 205n41)。
第三個基於意義的反對不朽的論點援引了敘事的考慮。如果一個人整個生活的模式非常重要,且一個合適的模式應該包括開始、中間和結束,那麼看起來永遠不會結束的生活將缺乏相關的敘事結構。“因為它會無休止地拖延,它遲早只會是一連串缺乏所有形式的事件......有了不朽,小說永遠不會結束......這樣的小說能有多大意義?”(May 2009, 68, 72; 另見Scarre 2007, 58–60)。請注意,這一反對與無聊和重複的考慮(涉及新奇)不同;即使一個人被激發並保持活躍,即使一個人找到了在永恆的過程中不重複自己生活的方法,不朽的生活似乎也會缺乏形狀。作為回應,一些人拒絕認為有意義的生活必須類似於小說,而是選擇以一種類似於彼此建立的一系列短故事形式的敘事性(Fischer 2009, 145–77, 2019, 101–16)。然而,其他人則試圖表明,永恆仍然可以是小說般的,認為重要的結局是其內容是什麼以及它與之前的內容如何相關的功能(例如,Seachris 2011; Williams 2020, 112–19)。
對不朽的額外反對意見指出它削弱了意義,但它們原則上比前三個較弱,因為如果成立,它們可以論證說一個永恆的生活會有代價,但可能不會完全遮蔽它的意義前景。例如,有建議說永恆的生活會缺乏珍貴感和緊迫感(Nussbaum 1989, 339; Kass 2002, 266–67),無法體現如為他人勇敢冒生命危險等美德(Kass 2002, 267–68; Wielenberg 2005, 91–94),並且無法從維持或拯救他人的生活中獲得意義(Nussbaum 1989, 338; Wielenberg 2005, 91–94)。請注意,至少前兩個理由主要取決於對不朽的信仰,而不完全是不朽本身:如果一個人是不朽的但忘記了這一點或根本不知道,那麼一個人可以欣賞生活並獲得勇氣的很大部分美德(反之亦然,如果一個人不是不朽的,但認為自己是,那麼根據這些論點的邏輯,一個人將無法欣賞限制並且無法體現勇氣)。
4. 虛無主義
前兩節討論了什麼會賦予人類生命意義的理論賬戶。雖然這些理論並不意味著一些人的生活實際上是有意義的,但這一直是提出它們的絕大多數人的假設。大部分程序是假設許多生活具有意義,然後考慮它們擁有或可能擁有的原因。然而,存在虛無主義(或悲觀主義)的觀點質疑這一假設。根據虛無主義(悲觀主義),原則上能夠賦予生活意義的東西對我們任何人都是無法獲得的。
虛無主義的一個直接理由是對生活意義具有決定作用的極端超自然主義和對精神領域存在的無神論的結合。如果你相信上帝或靈魂對生命中的意義是必需的,且你相信這些都不是真實的,那麼你就承諾了虛無主義,否認生活可以擁有任何意義。儘管這種虛無主義的理由在現代時代很突出(或多或少是加繆的立場),但在分析哲學圈中它已經逐漸衰落,因為極端超自然主義已被溫和的形式所取代。
當今虛無主義的最常見理由不訴諸於超自然主義,或至少不是明確地這樣做。一組想法訴諸於元倫理學家所稱的“錯誤理論”,這一觀點認為評價性主張(在此案例中關於生命的意義,或關於道德作為意義所必需)特徵性地假設客觀實在或普遍正當化的價值存在,但這樣的價值並不存在。根據一個版本,價值判斷經常分析性地包含對客觀性的主張,但沒有理由認為客觀價值存在,因為它們“將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實體或品質或關係,完全不同於宇宙中的任何其他事物”(Mackie 1977/1990, 38)。根據第二個版本,如果沒有一套能夠被所有理性探索者完全正當化的道德標準,生活就會無意義,但事實是這樣的標準對於總是可以合理質疑特定主張的人們來說不存在(Murphy 1982, 12–17)。根據第三個版本,我們持有關於道德和相關價值如意義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的某些信念,是因為它們對我們的祖先在進化上有利,而不是因為它們是真實的。人類被他們的基因欺騙成認為存在一種無私的、客觀的道德,綁定他們,所有人都應該遵守(Ruse and Wilson 1986, 179; 參見Street 2015)。為了評價這些論點,必須借鑒過去幾十年進行的複雜的元倫理學工作。
與錯誤理論論點支持虛無主義相對,有些論證接受客觀價值的存在但否認我們的生活可以展示或促進它們以獲得意義。這種方法的一個版本堅持,要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我們必須能夠為世界增加客觀價值,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因為世界的客觀價值已經是無窮的(Smith 2003)。這一觀點的關鍵前提是,每一片時空(或至少物理宇宙中的星星)都具有一些積極價值,這些價值可以被加總,且空間是無限的。如果物理世界目前包含無窮大的價值量,那麼我們所做的任何事都無法在意義上產生差異,因為無限加上任何數量的價值仍然是無限。質疑這個論點的一種方式,除了懷疑時空或星星的價值之外,是建議,即使一個人不能增加宇宙的價值,意義也可能來自於作為某些價值的源頭。
接受客觀價值存在但否認我們的生活可以獲得或促進它們以獲得意義的虛無主義的第二個理由是David Benatar(2006, 18–59)的有趣的“不對稱論證”支持反生育主義,這一觀點認為將新人帶入存在是不道德的,因為這樣做總是對他們來說整體上是不好的。對Benatar來說,存在的壞處(例如,痛苦)相對於不存在是真正的劣勢,而存在的好處(快樂)相對於不存在並非真正的優勢,因為在後者的狀態中沒有人被剝奪它們。如果確實不存在的狀態不比體驗存在的好處更糟,那麼,既然存在不可避免地帶來傷害,就跟隨而來,存在總是比不存在更糟。儘管這個論點以體驗性的善與惡為例,但它似乎可以推廣到非體驗性的善,包括生命的意義和反物質。關於這個論點的文獻已經非常龐大(關於最近的論文集,參見Hauskeller和Hallich 2022)。
Benatar(2006, 60–92, 2017, 35–63)提出了另一個支持虛無主義的論點,這個論點訴諸於Thomas Nagel(1986, 208–32)廣受討論的分析,關於人類個體能夠對其生活採取的極度外在觀點。存在著,用Henry Sidgwick的影響力詞句來說,宇宙的“觀點”,即考慮一個人的生活與所有時間和所有地點的相關立場。當一個人採取這個最外在的觀點,並考慮自己對世界的微不足道的影響時,自己的生活中很少有事情看起來重要。考慮到構成時空的數十億年和數十億光年,一個人在地球上的某個社會中做的事情在75年左右的時間裡就不會顯得很重要。儘管這種推理賦予了人類有限的意義類型,從個人、社會或人類的視角來看,Benatar既否認最大類型的意義——宇宙意義——對他們來說是可獲得的,也主張這使得他們的生活變壞,因此得到了“虛無主義”的標籤。一些人反對認為我們的生活實際上可以擁有宇宙意義,比如說,如果它們在上帝的計劃中扮演了角色(Quinn 2000, 65–66; Swinburne 2016, 154),是宇宙中唯一擁有尊嚴的生命(Kahane 2014),或從事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欣賞的有價值的活動(Wolf 2016, 261–62)。其他人自然堅持認為宇宙意義與評估人類生活無關,其中一些人否認它會是真正的意義來源(Landau 2017, 93–99),而其他人接受它會是,但維持這個好處的缺失不應被視為壞事或值得遺憾(在Benatar 2017, 56–62; Williams 2020, 108–11中討論)。
最後,一個與虛無主義有關的區別來源涉及生命意義的本體論前提,與價值論前提不同。或許最激進的,有些人否認我們擁有自我。我們確實缺乏自我嗎,如果我們確實如此,對我們來說有意義的生活是否不可能(參見Caruso和Flanagan 2018中的論文;Le Bihan 2019)?稍微不那麼激進的,有些人承認我們擁有自我,但否認它們以相關方式處於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有些人認為我們缺乏生命意義所必需的自我治理或自由意志,至少如果決定論是真的話(Pisciotta 2013; Caruso和Flanagan 2018中的論文)。非量子事件,包括人類決策,似乎是由世界的先前狀態所必需的,以至於沒有一個能夠是其他的,而我們的許多決策是無意識的神經機制的產物(而量子事件當然完全超出我們的控制)。如果我們的任何有意識選擇都無法避免,且都最終由外在於它們的某些事物所必需,那麼它們或許不足以賺得驕傲或欽佩或構成生活的敘事作者。作為回應,一些人堅持認為決定論與道德責任之間的兼容性以相當的力量適用於生命的意義(例如,Arpaly 2006; Fischer 2009, 145–77),而其他人則主張決定論與道德責任之間存在不相容性,但這並不適用於生命的意義(Pereboom 2014)。
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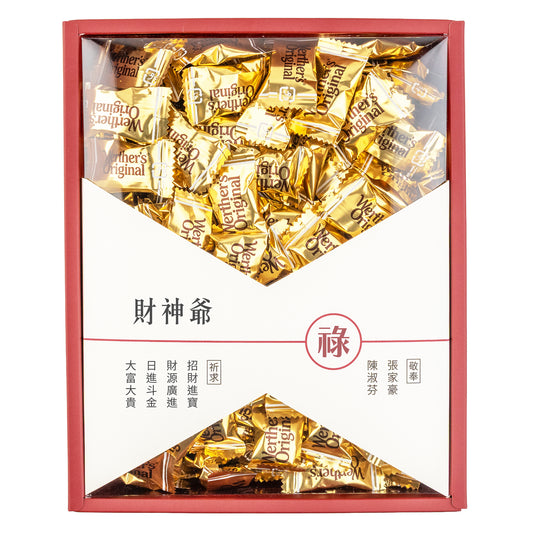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