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na Brown獨家專訪:談超級富豪與媒體權力風暴背後
Share
Tina Brown覺得超級富豪活該
奢侈的報帳額度。權力。誇張的墊肩!紐約媒體菁英的年代早已遠去,但在政治與文化這兩個領域裡,很難再找到比那個時期最顯赫人物之一——Tina Brown——更犀利的觀察者。1980與1990年代,她擔任Vanity Fair總編輯,開創出如今早已熟悉的一種混搭風格:既有充滿八卦味的好萊塢報導、上流社會醜聞,也有聚焦華府與世界各地戰爭的強悍深度報導。之後她掌舵The New Yorker,成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擔任該職位的女性。在那裡,她網羅了許多頂尖人才,包括後來在她離任後接下總編職位的David Remnick——當時她是離開去和Harvey Weinstein一起創辦命運多舛的月刊Talk(這份雜誌在兩年後便收攤)。
Brown之後又從高端光鮮的紙本雜誌世界,轉向較不那麼稀有化的網路領域,於2008年創辦The Daily Beast。她也寫書,記錄自己長年迷戀的對象——英國王室——以及她在Vanity Fair的歲月。如今,她把自己辛辣的政治與文化分析帶到Substack,在那裡撰寫一份既好看又充滿八卦味的電子報〈Fresh Hell〉(近期的標題包括:〈The Inside Story on How King Charles Pulled the Plug on Andrew〉以及〈Why Murdoch Doesn’t Give a Toss About Trump〉)。
Brown一次又一次重塑自己的能力,而仍保有一貫的敏銳風格,始終令我佩服。如今媒體與政治世界變動劇烈又充滿不確定,我覺得,和一位看得很長遠、故事又一籮筐的人好好坐下來談談,既踏實又有趣。現年71歲的Brown,果然沒有讓人失望。
我想先念幾段你寫過的「你」,唸給你自己聽。以下是你對幾位眾所皆知人物的描寫:Mark Zuckerberg,是「Meta’s slippery salamander」;Prince Harry,是「the ginger whinger」;你說Lauren Sanchez已經「proved that landing the fourth-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requires the permanent display of breasts like genetically modified grapefruit」。而你把我們的總統形容成「Tyrannosaurus Trump」。你是怎麼想出這麼辛辣的形容的?某種事情會在我手放上鍵盤時發生,而因為我現在寫的是這個Substack,我會進到另一個區域——是寫日記的那個自己。我不再覺得必須克制,對身為作家的我來說,這太讓人興奮了。我把自己想成生命的第三孕期,而不是實際的年紀。我感到被解放。另外,不再需要管理一大群人也很棒,因為我不必擔心:如果我想要那個人買廣告、或是想把那個人放上封面,這句話會有什麼後果。我現在可以盡情地寫。我覺得這很有必要,因為過去十年的寫作世界裡,實在有太多拐彎抹角、含糊其辭的文字。
你在1984年、30歲的時候就成為Vanity Fair的總編,對於我們這些沒那麼年輕就爬到那種高度的人來說,實在有點打擊。現在也有很多對那個年代的懷舊——書也好、文章也好、Podcast也好。你會想念那段時間嗎?嗯,關於懷舊這點,你說得完全正確。我大概在七、八年前寫了《The Vanity Fair Diaries》這本書,之後不斷有人跑來跟我說:「喔,我最近在讀,好懷念那個年代。」我想那是因為,那時候「工作」本身就超級好玩。現在好像所有的樂趣都被從工作裡抽走了。對今天的新聞與媒體來說,一切都變成:你要怎麼弄出一個有人願意看的平台?你要怎麼為它募到錢?你有哪些話會被某個贊助商不准你說?而我經歷的那段時期,則是不顧一切追逐精彩內容的年代,而我在其中玩得不亦樂乎。當時Vanity Fair的辦公室,簡直就是一個集合各種有趣、愛冒險人才的總部;The New Yorker也是一樣。我現在才意識到,自己在The New Yorker有多幸運——能和Art Spiegelman、Adam Gopnik、David Remnick、Jane Mayer等這些了不起的作家坐在一起,爭論我們在稿子裡要怎麼說,究竟公不公平、準不準確。我們談的那些事,全都跟「公司是不是要燒起來了」這類問題無關。不幸的是,年輕一代從踏入職場那一刻起,面對的就是這種「公司要不要完蛋」的焦慮,這實在太令人難過了。
我對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懷舊有個理論:即使網際網路讓資訊的取得方式、以及誰可以提供資訊都民主化了,人們還是開始渴望多一點「權威」。大家都想要有人帶路,帶他們穿過這一大片混亂。當然會這樣啊。所謂的把關者(gatekeepers)已經不見了。大家會說:太好了!彷彿把關者只是妨礙好東西出現的壞東西。可事實上,把關者同時也是品味制定者。如今沒有那些把關者,一切就變成一大團東西與雜質一起朝你奔來,你根本不知道去哪裡找好東西。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優秀的寫作其實仍然存在,只是要找到它像在大草堆裡找一根針。我常常有種「我到底錯過了什麼」的感覺;因為總有人會說:「欸,你有沒有看到那篇超棒的文章?」我心裡就想:在哪裡?我訂了一千封Substack,還在看社群媒體、舊派媒體,頭都快炸掉了。而這不幸導致的結果,就是很多人乾脆選擇退出、不再看。這是一個非常讓人洩氣的時代。年輕人常問我:「我要怎麼進入新聞業?」我常回答他們應該去印度,因為印度其實有非常活躍的文學文化。
我真不敢相信,你給人的建議竟然是「去印度」。[笑] 對,這個建議一點都不受歡迎。每次我說完,都看得出對方眼中的光瞬間暗掉。
我想稍後再回到你早期的職涯,不過你對一些當代議題也相當有權威,而那些事情的根源其實可以追溯到1980、1990年代。其一就是Jeffrey Epstein。[本次訪談發生在國會釋出新一批Epstein電子郵件之前。] 你認識Jeffrey Epstein,也在社交場合認識Ghislaine Maxwell。在你的書《The Palace Papers》中,你形容她在社交圈裡是無所不在的人物。當時你是怎麼理解她和Epstein之間的關係?當時我其實並不了解他們的關係,因為你幾乎從來看不到Epstein跟她一起出現。我認識她的那段時間,Epstein在她人生裡已經有點像後照鏡中的人影了。直到後來讀到相關報導,我才真正知道她和Epstein之間的背景。我認為她自己也是一個受虐者。她的父親Robert Maxwell是個非常可怕、專橫的人——既是報業大亨,也是騙子;但在一段時間裡,他這個騙子卻又是「世界之王」。她就是在這種「光輝大亨」的氣氛中長大,最後卻發現這個人其實是個騙子。那種創傷深深刻在她身上。我在寫《The Palace Papers》時挖到一個極好的故事:她還是小女孩時,曾帶一個人到她房間炫耀,梳妝台上整齊擺著數把梳子,她說:「Daddy讓我在他想打我時自己選其中一把。」他要她自己「策展」自己的懲罰。[在Brown的書裡,她對此的敘述略有不同,是幾樣物品與一把梳子一起擺在檯面上。] 我認為對Epstein,她是瘋狂迷戀的;而她覺得唯一能重新博得他歡心的方法,就是參與——並且最後親自「策畫」——他對年輕女性的虐待。但如果你只是看她在派對上穿梭工作的樣子,根本不會想到這一切。她活該在監獄裡待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你覺得她真的會在監獄裡待很久嗎?嗯,這點很有趣。如果臨走前Trump給她特赦,我一點也不會意外——等到MAGA已經不再重要的時候。但我認為如果他現在這麼做,一定會引發巨大的公憤。
2010年代初,你主導The Daily Beast時,做過全國最早一批關於Epstein的系列報導,後來你也提過,那些故事在當時其實沒有真的「黏住」輿論。的確沒有。真正改變一切的是#MeToo。Julie Brown在The Miami Herald做出那組精彩的系列報導時,已經是#MeToo之後了,人們開始更加、更加專注於權勢男性對年輕女性的侵害。我們刊登報導的那個時點,Epstein還不是那麼知名,他比較像一則圈內人的社會新聞——有個混在富豪圈的人,外界其實不太知道他是誰。這整件事顯示時代已經徹底不同。
那組系列報導裡有一篇標題是〈Epstein’s Society Friends Close Ranks〉。文章裡有人說:「A jail sentence doesn’t matter anymore」,又說:「The only thing that gets you shunned in New York society is poverty。」真是冷血到家。那卻確實是真的。他被判刑之後,我還曾被邀請去他家吃晚餐。有位公關打電話到我在The Daily Beast的辦公室,跟我說:「Tina,我想邀請你來Jeffrey Epstein家裡參加一場很棒的晚宴,其他來賓有Charlie Rose、Woody Allen和Prince Andrew。」Lloyd Grove——當時在The Beast工作的記者——每次見到我都還會提醒我,我當時在電話裡大吼:「這到底是什麼——the Predator’s Ball嗎?」我很憤怒,因為她顯然沒看過我們的報導。我對她說:「我已經刊出好幾篇關於這傢伙的文章了。非常謝謝,我拒絕。我一點也不想去Jeffrey Epstein家吃晚餐。」
你另一項專長是王室。Prince Harry和Meghan Markle正試著在世界上闖出自己的路,但他們當創業家似乎走得相當坎坷。你覺得他們現在還有什麼值得端出來的東西嗎?對他們身上發生的一切其實很令人難過。我從沒看過哪個專業人士像Meghan一樣犯下這麼多錯誤,而不幸的是,Harry也不是最亮的那顆燈泡。他原本以為Meghan會成為自己走出白金漢宮、面對廣大世界的導航者,結果事實證明,Meghan在職涯上是一個接一個做出可怕的決策。現在他們看起來到處都成了被排斥的邊緣人,這對他們來說非常艱難,因為本來美國應該是幫他們付帳單的地方。更可惜的是,Harry其實很擅長當一位王子——他很有魅力、樂觀又討喜,走進一個房間就能讓人開心,跟年輕人相處也很拿手。你把他送到世界任何角落,他都會受到歡迎、讓人覺得可親。我想他現在才太晚意識到,自己天生就是要當一位王子。而如今,他基本上只是個接公關案子的男人,而Meghan則在試驗她最新的料理點子之類的東西。看起來,Harry最好的選擇就是想辦法回到英國。我很希望有某種方式能讓他跟家人修補關係,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件事只會越來越難。我覺得最後做決定的人會是William,而我也認為William對整個局勢的看法非常強硬——在他眼裡,Harry的背叛是無法彌補的。
為什麼王室會一直是你感興趣的題材?當我寫王室時,也同時能寫到很多其他東西:階級、英國社會、名人文化。另一個讓我著迷的點,是一群有真實感受、傷痛與喜樂的真人,在一套有千年歷史的君主制度之下,持續上演的人性戲劇。他們跟你我一樣都是人,卻關在這個籠子裡,還得想辦法在籠子裡過一生。你甚至可以說,對現代人而言,這樣的處境幾乎殘酷得過頭。
我想再回到你主導那些大雜誌的時期。Vogue的傳奇總編Anna Wintour現在要卸任了。你在Vanity Fair和The New Yorker時,她也都在那裡。你們兩位都是打破許多藩籬的女性,同時代的同輩。你怎麼看她的傳奇與留下的遺產?Anna真的非常了不起。她從Vogue的總編,逐步成為整個公司的「連接組織」。我打從心底敬佩她。身處在同一個環境裡,看著它一變再變,那肯定有點像噩夢。像Condé Nast這樣的雜誌公司,從我們當年在那裡、在S.I. Newhouse Jr.掌舵的黃金年代,到如今,整個問題意識都徹底不同。我們當時真的很幸運,在一間私人公司裡工作,被允許專心做事、發揮創意。我想她現在有很多時間都被耗在企業的煉獄裡。所以,她一定真的很熱愛自己在做的事。
你會後悔當年離開Condé Nast嗎?她現在的地位已經完全定型,你原本也可以走上那條路的。我會後悔離開The New Yorker去跟Harvey Weinstein一起工作嗎?我可不覺得那是多聰明的職涯選擇!那點我當然是後悔的。不過此後我也過了一段非常有趣的人生。我這個人很難安分、創意旺盛,要我一直待著當Condé Nast的象徵人物,絕對不可能。
你在寫那段時期的文章裡也曾提過一些細節,而以我們對1980、1990年代的了解,我想那時應該相當性別歧視。我的確最大的挫折——而且那確實帶有性別歧視色彩,只是我當時沒這麼看,現在才意識到——是:即便S.I. Newhouse身為老闆有多麼優秀,我和他的關係仍舊非常居高臨下。他對我關於「這家公司應該怎麼經營」的看法完全不感興趣。我認為我們應該成立製作公司,應該舉辦影展、論壇、現場活動,我把一整套構想都攤給他看。他只是看著我說:「Stick to your knitting, Tina. You’re an editor。」整件事讓我非常沮喪。我現在覺得很振奮的一件事,是Bari Weiss創辦The Free Press,然後以1.5億美元賣給Ellison家族,接著她又去掌管CBS News。她被當成一個商業構想正確、有遠見又有趣的人來傾聽,這實在太好了。她說明了兩個時代之間的差異。
我們也該提一下,你的Substack文章曾被轉載到The Free Press。沒錯。我其實很欣賞他們。
我本來很好奇,你會怎麼看她。我覺得Bari看見了人們對woke文化越來越不耐煩,然後順勢把這股情緒當成通往高處的火箭。她以那股不滿為核心打造The Free Press,而且做得很好。不過現在她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Trump的世界已經把那整個概念,扭曲成更加醜陋的東西。我認為這會變成她極大的考驗,特別是現在她成了CBS的掌舵人。當第一通來自白宮的電話打來,說他們討厭那篇正在準備中的報導,而她理應要捍衛新聞專業時,她要怎麼做?那會非常、非常困難。如果當時由我給她建議,我會說:「拿The Free Press那筆錢,但別去接CBS。」不過,她並沒有來問我意見。
接任你成為Vanity Fair總編的是Graydon Carter,他最近出了回憶錄。他寫說,自己在那裡的前兩年相當糟糕,部分原因是『留下來的Tina Brown盟友非常敵意、也很具顛覆性』,還說他到任時,『幾乎找不到任何一篇讓我覺得值得出版的稿子』。看到這些你有驚訝嗎?其實我沒看那本書,因為在書到我手上之前,我已經聽太多人談論過,結果反而不想看了。你看,我離開時留下了一整個團隊,他們是否「顛覆」我完全不知道,我也跟那些事毫無關係。至於說「幾乎沒有值得出版的東西」,這點倒讓我很訝異,因為當時其實有不少很棒的稿子還擺在那裡。不過,他自己後來做得很好。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到現在還對我懷著一種古怪的怨氣。
他還寫到,他聽說雜誌的style director會去你家,幫你搭配當天要穿的衣服。當然,她的確會來啊。
這是真的?她每天早上都會過去?才不是每天早上呢!如果那天我要去什麼大場合,我當然會請她過來幫我。為什麼不呢?她在衣著品味上比我好太多了。
你覺得他為什麼要提這些事?這就是典型看待女性的性別歧視視角。那是一種居高臨下的神話,讓男人在面對我們時感覺好受一點——因為我們其實很具威脅性。於是,我的成功就必須被包裝成某種貶低式的「Rockette形象」。過去真正讓我覺得好笑的是,當我以編輯身分得獎時,頒獎詞總是比男性得主荒謬許多,大概會是這種:「Tina Brown是那位buzzy、irreverent的編輯。」明明我才剛刊出一篇三萬字、關於薩爾瓦多暴行的報導,我卻依然是那個「buzzy」的存在,好像我是某種康康舞女郎一樣。
我看過你說,你非常討厭「buzzy」這個字。那是個很傻的詞。所謂的buzz,不就是代表人們在討論你寫的東西嗎?難道我們想要的是一片寂靜?你會想把作品丟進宇宙黑洞裡嗎?所以我有時會在信末署名:「The erstwhile queen of buzz。」
你怎麼看現在這個媒體時刻——媒體機構和有錢人之間的關係如此緊繃?像L.A.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還有Larry Ellison之子David Ellison這種世界首富之子,如今掌管Paramount和CBS。你覺得這類人為什麼要涉入新聞業?老實說,我已經被這些超級富豪煩透了,他們總以為自己有錢,就什麼都懂。他們對我們這個行業極度不尊重,對我們一點敬意也沒有。這正是我對那些數位霸主最大的怨氣所在。坦白說,我大概任何時刻都在為這件事悶燒。
現在媒體圈裡,你覺得最讓人厭惡的人是誰?喔天啊,太多了。我對Jeff Bezos非常失望。我原本把他視為The Washington Post的大救星,結果看起來他整個180度大轉彎。Tucker Carlson則讓我完全摸不著頭緒。他以前在Talk Magazine替我工作。
真的嗎?是啊,我當時的兩位政治記者就是Jake Tapper和Tucker Carlson。Tucker以前是個非常好的寫作者,我當然樂意讓他進The New Yorker。他對文字轉折有極佳的天賦,也有一雙諷刺的眼睛,他真的很出色。然後某件奇怪的事發生了——彷彿他被人換了顆頭,變成那種口沫橫飛的瘋子。我完全不懂他身上發生了什麼。我想這個時代真正讓我震驚的,是人們變化之快。
說到政治,就不得不提你所認同的城市紐約剛經歷的一場大地震:新任市長Zohran Mamdani,讓財閥階級嚇得要死。他能做到這點實在太棒了。他們真的被嚇壞了。
他之所以崛起,你覺得說明了人們對菁英階級的感受有什麼變化?那是一聲絕對非喊不可的戰鬥號角。這幾年,我們真的被超級富豪霸凌得很慘。彷彿凡是公共辯論——不論是學界、國家該怎麼治理,或是科技革命下我們的生活方式——能發聲的永遠都是有錢人。我認為,人們對於那龐大的財富與幾乎無法對抗的現實,感到越來越絕望。Mamdani示範了如何把戰鬥意志搶回來,那非常鼓舞人心。金錢並不能買到一切。那麼多錢砸下去想把他擋掉,他最後還是贏了。就算你不喜歡他的主張,也應該為此感到高興。我自己就非常高興。
你覺得接下來會怎麼發展?我認為我們一直低估了人性本身的力量——這正是Mamdani所展現的。我們過去總以為未來只有一個方向:AI、那些超級財閥會決定我們要怎麼活,而其他人都只是農奴。所有這些想像都讓人非常沮喪。但也許,人性蘊含的能量,比他們預期的還多。美國的局勢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完全翻轉,這也是我熱愛住在美國的理由之一,那是一個很刺激的地方。整個社會的情緒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掉,大家突然就會說:等等,我不想讓你來決定我的人生該怎麼走。所以此刻我其實相當樂觀。
最後一題:這篇訪談的標題應該是什麼?「Dinosaurs Still Rule the Earth?」——句尾要打問號。
喔,不,我覺得至少要用驚嘆號。你本人就是一個驚嘆號。好吧,那謝謝你了,Lu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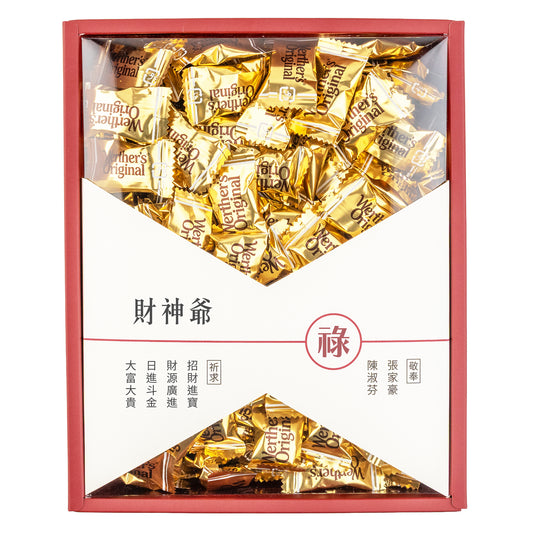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