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里斯多德的勇氣哲學:在恐懼中守住正義與靈魂自由之路的選擇
Share
Aristotle為我們勾勒出一套勇氣藍圖,好讓我們即使冒著自身風險,也能抵抗不義並做對的事。
高約四英尺、以青銅打造的Kristen Visbal雕像Fearless Girl,以堅定的神情直視紐約證券交易所(這座雕像原本安置在紐約金融區、Arturo Di Modica的Charging Bull對面)。她那帶點頑強、勇敢頂撞的姿態,具體表現出作品標題中所蘊含的理想:無所畏懼。我們會稱讚運動員或行動者「fearless(無畏)」;廣告活動與T恤標語則鼓勵我們「be fearless(成為無所畏懼的人)」。我們之所以欽佩「無畏」,並不是因為它本身,而是因為我們把它與「勇氣」這個德性連結在一起。勇敢的人似乎在追求有價值的目標時,特別不受恐懼所束縛。美國作家Ralph Waldo Emerson就表達了這樣的直覺,他把勇氣稱為「不被任何恐懼動搖的完美意志」。
然而,也可能有人會主張,使勇敢如此令人欽佩的,並不是「沒有恐懼」,而是勇者能夠「儘管害怕仍能行動」的能力。我們稱那些為拯救他人而冒著生命危險的消防員「勇敢」,看起來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可怕的危險面前毫無所動,而是因為他們明明感到害怕,卻仍然向前邁進。因此,問題就出現了:勇氣,是在於「毫無恐懼」,還是在於「以正確的方式感受恐懼」?
古希臘哲學家Aristotle在探討勇氣這項德性時,也遇上了這個難題。在《Eudemian Ethics》中,他一開始把勇敢的人視為「不懼怕的」(希臘文aphobos)。但接著,他又提出一個相反的看法:如果勇者面對的是讓其他人感到膽怯的事物,而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可怕,那麼「人們會說,那裡面沒有什麼值得尊敬的地方」。要理解Aristotle如何在這兩種答案之間找到出路,我們需要先看看他的德性與情感理論。
在較為人熟知、討論美好人生的著作《Nicomachean Ethics》中,Aristotle說明:倫理德性是一種良好的性格狀態,是經由習慣養成的,它讓我們在塑造生命的各種情緒與活動中,能夠以優秀的方式來感受與行動。無論是讓人血脈賁張的憤怒,或是感官享樂那種誘人的牽引力,倫理德性都使我們能在特定情境中,適切地感受情緒:在適當的程度、適當的時間、關聯於適當的對象與人、出自適當的理由,並以適當的方式來體驗情緒。如果我們把情緒想成自然事件,像風暴在我們身體裡翻騰掠過,這種說法聽起來或許有點怪。在那樣的觀點下,情緒並沒有「對」或「錯」之分,因為我們無法掌控它們。然而,Aristotle認為,透過習慣與練習,我們可以學會如何以正確的方式來感受情緒。
勇敢的人有可能失去很多,但他們也有能夠獲得的東西
以Aristotle所談的勇氣德性為例,它用來調節「恐懼」與「自信」這兩種感受。和所有倫理德性一樣,它是在過度與不足兩端之間的一種中庸狀態。勇者介於懦弱者與魯莽者之間:懦弱者過度恐懼(而自信不足),魯莽者則過度自信。與可能在恐懼上走向極端的懦弱者不同(可能是感到過度恐懼,或是害怕錯誤的事物,等等),勇敢的人有一種獨特的傾向,能以正確的方式感受恐懼(也就是: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程度,出於正確的理由,去害怕正確的事物)。
Aristotle並不認為,只要面對任何令人害怕的事物就算展現勇氣,也不認為害怕很多事物就一定是懦弱。(他說,有些事如果不去害怕反而是錯的,例如蒙受恥辱。)亞里斯多德式的勇氣針對的是特定的恐懼對象;勇者認為某一類特定的恐怖值得面對:也就是對死亡,或是對嚴重而痛苦創傷的恐懼。而且並非任何死亡皆然——最完滿的勇敢行動,是在面對「高貴的死亡」時仍堅守陣地,這份高貴特別體現在戰場之中。
他對「高貴的死亡」的強調,對現代人來說或許有些古老而疏離,不過這樣的說法幫助我們凸顯勇氣(以及一般德性)的其中一項關鍵特色:也就是德性之人的動機。具有德性的人,都是為了Aristotle所說的kalon而行動:也就是「高貴」、「美好」或「優雅高尚」的事物。就算有人在海上或面對疾病時顯得毫不畏懼——這或許同樣值得讚賞——若他們行動的理由不是因為「這樣做很高貴」,而只是因為「這樣做很有用」,那就不算展現出勇氣。
因此,亞里斯多德式的勇氣,比起「在致命危險前控制恐懼」這樣寬泛的說法,要具體得多。一名在戰場上堅守不退的士兵,若是因為害怕軍紀處分或害怕蒙羞而不敢撤退,他並不是真正的勇者;真正的勇者,則是在那個時刻,正是因為「這麼做很高貴」,才選擇在戰鬥中站穩不退。勇敢的人的確有可能失去很多(包括他快樂而有德性的生命)。但他同時也有能夠獲得的東西:就是完成一個kalon的行動。我們可以延伸這套說法,在現代尋找類似亞里斯多德式勇氣的例子:例如,一位政治行動者在根深柢固的壓迫下,仍為爭取公民權利而抗議,即便危及自身自由,因為她相信那才是對的事;又或是消防員冒著自己的性命危險衝進燃燒的建築物,只為拯救他人的生命,因為他相信那是正確的抉擇。
那麼,勇氣究竟是「毫無恐懼」還是「善用恐懼」?在《Eudemian Ethics》中,Aristotle說,勇者在面對「無條件可怕的事物」時是「不害怕的」,雖然勇者可能會對一些事物「稍微害怕」或「不常感到害怕」——而在面臨巨大危險時才真正感到恐懼——但他的意思似乎是:勇者在展現勇行時,感受到的恐懼很少,甚至幾乎沒有。在《Nicomachean Ethics》中,他說勇敢的人是一種「不懼怕的類型」(aphobos),而且他們在面對「高貴的死亡」時是「無所畏懼的」(adeēs)。或許,對勇氣而言,「適當的恐懼量」就是完全沒有。
然而,如果這真是Aristotle的看法,那就很難和他另一個主張調和:也就是有些人是「過度無懼」的。所幸,他的理論其實細膩到足以納入「帶著勇氣的恐懼」。在《Eudemian Ethics》中,他把勇氣比作力量:正如一名強壯的運動員可能會被非常激烈的訓練所耗盡,但不會被一般人就足以累垮的運動弄得疲憊一樣,勇者也會害怕極端的恐怖事物,只是那種程度的恐懼,遠超出一般人日常所見的那些。他們對恐懼具有特別強大的耐受力,但並非完全不受影響。
雖然勇者已經是人類所能達到、最「不輕易被嚇倒」的存在,Aristotle在《Nicomachean Ethics》中說,他們不只會害怕那些超出人類能力範圍的可怕事物,也會害怕那些「在人類層次上」的恐懼:
勇敢的人也會害怕這類事物,但會以正確的方式去害怕,並且依照理性所判斷的那樣去承受。他們的目的,是做出高貴的行動,因為那是德性的目標……那些在人應該害怕與應該鼓起勇氣之處,以正確的方式、出於正確的理由、在正確的時間承受恐懼並鼓起勇氣的人——這些人就是勇敢的。(採Susan Sauvé Meyer的英譯)
這個讓步對Aristotle理解勇氣的方式至關重要,一方面他承認勇者在展現勇行時確實會感到恐懼,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對勇氣觀點的複雜性。他的重點不只是說「勇者能很好地承受恐懼」,而是說他們並不把恐怖的事物視為「必然要避開勇敢行動」的理由。勇敢的人反而是追隨理性,並且以正確的方式、為著高貴之事而忍受可怕的情境。
恐懼可以讓心智聚焦在避免危險所需的關鍵步驟上
讀者有時會覺得難以理解Aristotle的說法:他使用「忍受」可怕事物的語言,似乎暗示勇者必須對抗並克服自己的恐懼。如果真是如此,那勇氣就會包含一種Aristotle明白否認的內在拉扯與衝突。他堅持說:「如果你能忍受可怕的事物,並且因為這樣而感到愉悅——或至少不感到痛苦——你就是勇敢的。」(Meyer英譯)然而,Aristotle並不認為恐懼是我們必須對抗或壓抑的東西,否則就會導致內心的撕裂與煎熬。相反地,勇敢的人會把恐懼納入自己的行動之中:他們會把恐懼放在正確的視角裡,並善用恐懼來成就一個高貴的目的。他們懂得「好好害怕」。
恐懼可以讓心智聚焦在避免危險所需的關鍵步驟上。對Aristotle而言,以正確、具有德性的方式感受恐懼,並不會驅使我們「不計代價地逃避危險」,也不會促使我們「毫無顧忌地衝向危險」,而是會引導我們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例如穿上盔甲),好在追求高貴目標的同時,面對並承受那些危險。勇敢的人不需要不斷壓抑自己「想逃離高貴死亡」的衝動;相反地,他們的恐懼會提醒他們:周遭有哪些真正關鍵的危險,而他們則依照理性,採取謹慎的作為,一邊迎向那些危險,一邊為高貴之事而行。
與青銅雕像不同,Aristotle筆下的勇者並非刀槍不入。他清楚而痛苦地意識到:追求正確的行動,確實會讓自己暴露於「真實的損失」之下。勇敢的人之所以特別突出,是因為他們有能力選擇高貴之事,即便代價是放棄生命中的其他好處——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包括他們自己的存活。因此,Aristotle向我們展示了一件既困難又令人敬佩的事:那是一種面對恐懼的方式,能夠把我們「逃離痛苦與損失」的本能衝動,轉化成一種理性的前進,使我們得以守護德性。
我們可以把這個教訓運用在遠離戰場的艱難抉擇中,包含捍衛政治共同體的完整性。未經教育的恐懼,會驅使公民為了安全感、物質利益或社會優勢,而犧牲正義。這也說明了:為何在Aristotle的時代──以及在我們的時代──暴君會透過恐懼與對生活福祉的威脅來維持權力。如果我們想擁有一個有能力為抵抗不義而做出犧牲的政治共同體,那麼,這個共同體中的某些成員就必須懂得如何「好好感受恐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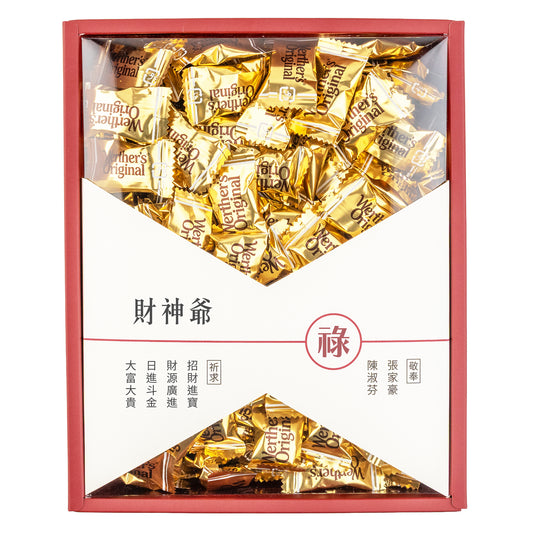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