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取向多樣性:演化如何塑造我們的愛
Share
演化提供了一個新答案
人類是多樣性的繽紛光譜,特別是在性別事務上。只需看一眼不斷擴大的縮寫LGBTQIA2S+,就涵蓋了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酷兒、雙性人、無性戀者和雙魂人。調查表明,我們中的2%到10%傾向於同性吸引,不論文化界限。但為什麼這種性別少數的馬賽克在全球各地文明中持續存在呢?
簡而言之:這是演化的手筆。同性行為不僅僅是我們獨有的;它橫跨脊椎動物甚至昆蟲。在我們這個物種內,性取向多樣性很可能在某些歷史背景下服務於一個適應性目的。這一理論從最近發表在《科學進展》上的一項開創性研究中獲得支持。
深入英國生物銀行的寶藏,作者Siliang Song和Jianzhi Zhang來自密歇根大學,揭示了一個迷人的景象。他們的發現揭示,與他們的異性戀對手相比,雙性戀和同性戀男性往往走上了一條擁有更少孩子的道路,或者用演化的行話來說,達爾文健康度較低。然而,雙性戀男性在這方面受到的損失較小。
但是,損失就是損失,你可能會說。雙性戀男性如何彌補他們與異性戀男性之間的這種健康差距呢?
這讓我們回到了一項早期的研究,顯示攜帶同性戀基因的異性戀者傾向於擁有更多性伴侶。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古老和傳統社會不是一夫一妻制;因此,擁有多個伴侶的男性留下了更多後代,將他們的遺傳遺產傳播得很廣。
想想歷史人物,如Moulay Ismael the Bloodthirsty,據稱生了888個孩子,或者像成吉思汗或西班牙征服者那樣基因廣泛傳播的人物。但在這些極端案例之外,通常是男性的冒險精神與更多的性遭遇和因此更多的後代相關聯。
那麼,這與雙性戀基因有何關聯呢?好吧,這些基因似乎不僅使人們傾向於雙性戀行為,還傾向於冒險傾向。這種聯繫是關鍵,特別是在前現代社會中,冒險的男性更有可能廣泛播撒他們的野生種子。因此,與男性雙性戀相關的大膽基因不僅關於性偏好;他們還提供了一個健康優勢,正如研究人員恰當地將它們描述為“生殖上有利的”。
Song和Zhang的發現也描繪了一個鮮明的現實:雖然現代的同性戀女性現在可以選擇人工方式懷孕,但只喜歡自己性別的同性戀男性面臨著對他們的生殖健康最嚴峻的打擊——他們面臨著空搖籃。但我們如何通過演化的視角來調和他們的存在呢?
一種情景表明,在異性戀個體中潛伏著一些攜帶與同性戀相關的基因的人,他們踏上了大膽探險的道路,通過一系列冒險將他們的血脈播種。因此,如果我們思考一些歷史上的偉大征服者可能攜帶同性戀基因的可能性,這並不遙遠。
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值得探索。
想想社會性蜜蜂、黃蜂、螞蟻和它們的哺乳動物對應物——裸鼴鼠。大多數是勤勉的工作者和無畏的防衛者。儘管他們在維持殖民地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他們不直接繁殖。相反,他們將這項任務委託給女王。這種策略依賴於殖民地成員之間的共享基因。當女王繁殖時,她不僅傳下自己的基因,也傳下那些與她共享基因的人的基因。所以,每個人都獲得了。
通過基因親屬傳遞基因稱為親屬選擇。把它想象成像三項全能、七項全能或十項全能這樣的多項目體育盛事。勝利不取決於贏得每一個個別項目;它關於累積最高的總分,即使你沒有在任何單一比賽中取得第一名。
在這場基因遺產的遊戲中,人類也長期依靠親屬選擇來傳遞我們DNA的共享線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本能地向我們的基因親屬延伸善意和支持,樂於為了我們的子女、孫子孫女、侄子侄女和堂兄弟姐妹的福祉而犧牲我們的時間和資源的原因。
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經常體現在大家庭或宗族和諧共處中,已經是而且繼續是親屬選擇的庇護所。在這些緊密聯繫的圈子內,不直接參與繁殖也有機會增強我們的遺傳健康。這種精神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在某些傳統農耕社會的東南亞,一位年輕母親可能選擇殺死她的第一個新生兒,如果他是一個兒子,相信一個女兒可以更好地幫助養育她期待擁有的許多後代。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是那些專門喜歡同性伴侶的人也可以找到他們的基因繁衍的立足點。
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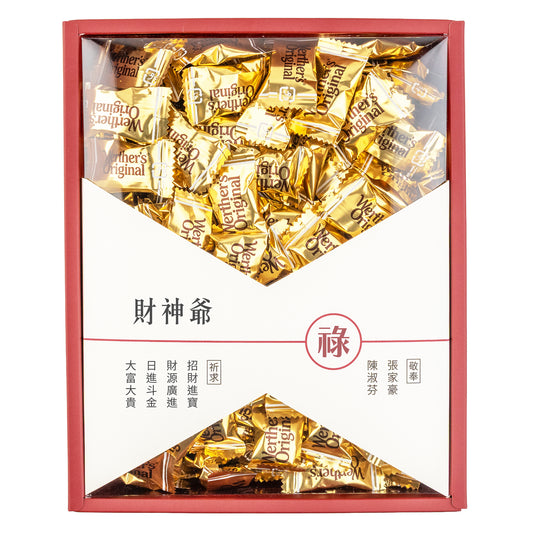














![燙金小囍字貼紙 [24枚]](http://wish.with.tw/cdn/shop/products/hqdefault_2cb3b4c8-ec0a-453e-a8be-1b14dad58faf.jpg?v=1619698098&width=533)







